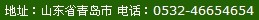|
北京中科医院在哪里 http://m.39.net/pf/a_4703213.html作者梁敢雄考证赤壁战址必须重视的方法论问题——《汉末赤壁之战的历史真相及其流传史》之绪论摘录小引:鉴于群友梧桐提出关于要跳出黄州考赤壁的方法论问题。其实,在待版拙著八千字绪论中对考证赤壁的方法论已有系统阐述,其重点是从史料的可靠性上入手,首先证伪了南北朝盛弘之与郦道元的赤壁、乌林之说。当然也对跳出黄州考赤壁的问题有所澄清。特从绪论中摘录方法论之阐述,以答群友。绪论摘要东汉建安十三年即公元年,江汉流域发生了两场特大的军事事变。前-场是曹操率领大军30万(此乃四十多年后吴国当政的诸葛恪对群臣公布之数)号称80万人马南征,荆州刘琮望风而降。如不计刘琦控制的江夏郡残余的江北数县外,曹军几乎占领了汉南江北全境,荆州江南四郡虽未军事接管却已传檄而定。由于《三国志·魏书》之所载诸将传中,几乎凡隨曹操南下荆州者皆称为“从征荆州”,故这一重大事变可称荆州之降。曹操在荆州首府襄阳花了两三个月时间完成“更始”后,另一大军事事变隨之发生——曹操趁此时北方已基本统一、荆州不战而轻易得手且经“更始”已经稳定,力图利用此大好时机统一全国。因此拒绝了谋士賈诩关于善治荆州、抚安百姓而等待江东稽服的建议,一面下战书给孙权曰:“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一面亲率大军包括荆州降军,水陆俱下,征讨江东孙权及投靠孙权的刘备。在现存魏晋时代的史料中,对于这场败曹、破曹的赤壁之战所在地的位置,除汉末王粲在《英雄记》结合西晋人的《江表传》而有大致的界定外,其他记载均很笼统,只言在赤壁(只有东吴也称其为乌林)、所示方位很不具体,然而没有意见分歧发生。因为魏晋人距赤壁之战时间很近,而当时江边耸立的赤壁这一特殊的地质地貌现象似乎很出名、人们很熟悉其所在地,似乎觉得用不着指出赤壁所属县的县名来。但从现存魏晋大多数史料还是可以明显地看出:赤壁决战战址大的范围应该在曹军屯兵的长江北岸!从亲历者王粲在《英雄记》与西晋人的《江表传》的描述,则可进一步把赤壁界定在汉水出江口与樊口之间。东晋史官袁宏的《东征赋》与干宝的《搜神记》二者都揭露出鄂县樊山沿江一带是赤壁之战中孙吴破曹的前沿阵地(由此可知曹军阵地在对岸不算远处),此战之胜奠定了东吴立国的“初基”(袁宏语),故东吴正式立国时立即废鄂县旧名、命新名为武昌并迁国都至此,以示此地使东吴以武而昌。结合刘备、刘琦先后撤退至江南鄂县之樊口以及黄盖在江南可“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不难想见曹军“引次江北”,其屯兵似应在夏口下游、樊口上游不算太远处。否则:①由于《三国志》记载了赤壁战前夏口曾为孙吴攻陷过的刘表重镇,又曾是刘琦刘备进住屯兵之处,若曹操大本营屯于此,《三国志》不能不有记载;②若曹军引次于夏口之上,则距刘备屯军的樊口和晋代《东征赋》《搜神记》所揭示的东吴屯兵樊山一带太远,则双方不能夾江对峙而成彼此脱离的形势,黄盖也无从观察到曹军舰首尾相接。总之,我们必须以汉末魏晋时的史料作为赤壁战史的最可靠的核心史料,此时人们对赤壁战址、交战的阶段、决战时日尚未产生分歧与争论。至于南北朝以降的史料则大不如汉末魏晋史料可靠了。因为南北朝已距赤壁之战两、三百多年,人们已弄不明白赤壁有何独特景观?它究竟在何郡何县?虽有极少数尊重历史事实、补充赤壁战址具体方位的新史料出现,更多见的则是以个人揣测代替史实、或者以讹传讹,从而导致赤壁战址异说蜂起。南北朝时期先后出现的指定赤壁之战具体地址流传较广的新说法、如不计晋宋间人范晔据魏晋史料订正的曹操败之于乌林、赤壁说外,有:⑴刘宋盛弘之的蒲圻县沿江百里南岸名赤壁说;⑵北魏郦道元的江北百人山对岸的赤壁山说(即后人所谓江夏说或曰武昌说);⑶梁朝庾信的樊山钓台斜对岸的黄州赤岸说;⑷六朝人的汉阳临嶂山说与⑸汉川赤壁草市说等等,不下五种之多。这五种所指赤壁战址的方位都较为具体。唯范晔所言败曹于“乌林、赤壁”之说由一地变为二地难免使人生疑,但它却有其独特的贡献:即范晔对《三国志》中的《吴书》不加任何区分地交互使用赤壁之役与乌林之役这两个地名概念,从而大有一地二名之嫌,作出了新的澄清与补充(参见第三章课题七)!后世学者记述赤壁战址的具体位置,往往对汉末魏晋的史料尊重不夠,大多各取南北朝史料中某一具体说法为依据。如唐宋至今关于赤壁战址有如下多种说法:江夏赤矶山说、蒲圻石头关说、黄州赤岸说、嘉魚东北江滨说,以及汉川赤壁草市说、汉阳临嶂山南峰说、蒲圻西良湖侧说、钟祥汉水岸边说等等。这就是说至今仍流传的赤壁战址的诸法,它们或多或少、或明引、或暗引都依据了南北朝时的某条史料。因而要想澄清赤壁战址的真相,就必须正本清源,必须以赤壁之战亲历者的描述和魏晋时的史料为基本依据,对南北朝时出现的史料必须作充分地比较、鉴别后,加以去伪存真,以达到拨乱反正的目的。而绝不能盲目地、无条件地信从它。因此,本书将有关赤壁之战的史料的搜集和分类,重点放在汉末魏晋时期;其次对南北朝史料则侧重与汉晋史料比照、甄别以定取舍。至于唐宋以降的文字史料,由于出现在赤壁之战后至少几百年之后,虽然其对赤壁之战的规模、阶段、性质、意义等等方面不乏新的认织,但除极少数人能结合实地考察提出某些新见解、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外,一般人对于赤壁战址及曹操进军与撤退之路线已鲜能提供有价值的证据了!说实话,唐宋以降的人们,在论及赤壁决战地址及曹操进军与撤退路线时似乎很多人缺乏认真的研究!他们中不仅很少有人认真考虑其说是否与魏晋典籍(如《三国志》、《辨亡论》《江表传》《华阳国志》《后汉纪》等)的可靠论述相合?更无人仔细斟酌其赤壁战址说是否与充当曹操秘书班子的亲历者建安诸子以及东吴两代当政大臣之子孙—陸机等对赤壁之战的追述吻合?大多数人只是从南北朝史料中取其一说(多取南北朝时出现较早的新史料之说)为据罢了!完全不管它与上举诸多汉末魏晋史料的可靠记述是否相抵牾、甚至是唱反调。有些论者似乎提出了具体的新见解,例如初唐时《括地志》提出“蒲圻县有赤壁山,即曹公败处”,又如李贤注《后汉书·刘表传》中“败曹公于赤壁”曰:“赤壁、山名也。在今鄂州蒲圻县。”这似乎是他们提出的新见解,却未能提供史料证据。有识者一眼即可看出二者不过都是暗袭了刘宋朝盛弘之《荆州记》关于蒲圻赤壁的说法仅小有订补罢了。盛氏是将赤壁指为沿江百里的南岸名,而《括地志》与李贤注则修订为赤壁只是蒲圻县内的一座山。既然两三百年后的南北朝的文献已经出现了较多的意见分歧而莫衷一是,时至今日是否可寄希望于用现代科学的手段——㈠依据考古发掘来断定;㈡依据地形、地貌的科考——来对流传的诸种赤壁战址说一一作出鉴定呢?窃以为可能性极小!先说现代考古发掘吧:因为对于古城、古墓、古建筑等古迹而言,只要其实体尚有残存,就可将其发掘出来加以考古鉴定。但战争地址这一概念,它又有何种实体能遗留下来呢?能遗留下来的无非是大量士兵尸体与大量残存的兵器而已。这就至少有如下两个必要条件之一出现,才有作出考古鉴定结论的可能:①较大范围内出土了赤壁之战遗存的古尸;②有大量的可断代为赤壁之战遗存的青铜兵器出土。但能满足这两种条件之一者其出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先就古尸说吧:它是否是更早时的士兵尸体(如赤壁之战前孙吴多次破黄祖,黄祖大量阵亡士兵的尸体)或者是后代的乱葬岗中遗留下来的尸体?更何况赤壁之战发生在南方江汉流域,这一带气候潮湿、夏秋炎热,当年赤壁之战阵亡士兵的尸体,到了一千八百多年后的今天,其骸骨早已腐蚀难存,又岂能指望它现形出土?再拿出土的汉末青铜兵器说吧:何以见得它是赤壁之战所遗留的兵器?而不是此前或者此后(甚至仅十几年后)才遗留下来的呢?有学者称今蒲圻赤壁即一带出土了多件青铜兵器,“大量的是东汉、三国时期的兵器”。然而今号称赤壁的蒲圻石头关与孙吴著名的军事重镇陆口(《三国志》提到陆口不下十多次)距离仅几公里左右。据《三国志》多传记载:陆口在赤壁之战后一度为孙吴所占而成为与刘备争夺江南诸郡的大本营,孙权曾驻此节度诸军,孙吴先后有多名将帅如鲁肃、吕蒙、陆逊、潘璋、吕岱、吕凯等均在此屯兵过,故陆口至蒲圻石头关一带长期是孙吴驻军练兵的场所。因而在这一带出土了大量遗存的青铜兵器很正常,与赤壁之战并无直接关系!谈到用出土文物证明赤壁战址,早在一千几百年前的唐代黄州刺史杜牧已开先河:杜牧在唐会昌二年至四年间(-)任黄州刺史,他在黄州江滩上发现了一支断戟而作有《赤壁》怀古诗一首曰:“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杜牧本来很推崇其祖父杜佑的名著《通典》,如他在黄州《冬至日寄小侄诗》中称“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诗中的“家集二百编”正是指乃祖的《通典》二百卷。然而正是这部《通典》称曹公军败於赤壁之处在蒲圻县!杜牧由于在黄州江滩中发现了汉末遗物—折戟,经磨洗而识别出有曹操或周瑜的标志痕迹,才果断地订正了乃祖的说法,认定赤壁之战发生在折戟出土之地——黄州!有人硬说这首《赤壁》诗是杜牧游览蒲圻赤壁后才写的!且不说蒲圻赤壁在唐代只称为石头驿或石头关,从来不是诗人题咏的游览地;而且杜牧还另有《齐安郡晚秋》诗言赤壁战地在本郡内,而齐安郡则是始自唐天宝元年延续了四十多年黃州之改称!瞎指杜牧《赤壁》诗写蒲圻赤壁显然是荒谬的。杜牧据实地发现的出土文物结合他早年读过庾信《哀江南赋》等文献而修订了其祖父关于赤壁战地的说法,大有近现代学人推崇“双重证据法”之风。远在唐代的杜牧能有此卓识,实在不简单!然而仅凭一只断戟出土似尚不足以断定其出土地必为赤壁战址,况且杜牧发现的这支断戟并沒有把它保存下来。由以上蒲圻出土兵器与杜牧在黄州江滩发现汉末断戟二例可见,对赤壁战址的判定,恐怕很难靠现代考古发掘所能一锤定音。当然,考古发掘有可能对涉及赤璧之战的某些问题能作出客观的判断,从而有助于对赤壁战址具体方位的认定。例如潜江龙湾的楚国章华台遗址的出土,结合章华台在两汉华容县内的文献,即可判明曹操经巴丘逃回江陵前所步行的最后一段路——华容道,在今潜江西北部而不在监利县,也不能如今天许多论者所论:似乎曹军一逃离赤壁就上了华容道!又如现代的地质勘探已判明古代云梦泽全在大江之北而否定了古人所谓“江北为云、江南为梦”的说法,从而有利于揭示曹操的撤军路线究竟在大江之北还是在大江之南。但是恐怕不能指望它对赤壁战址的具体位置作出直接的界定。再说是否可用地形、地貌的科考,来对流传的诸种赤壁战址真伪说作出鉴定呢?由于地形、地貌的类似性较多,恐怕“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难让抱定某种偏见者放弃己见。最明显的例子:湖北洪湖市历史上长期是云梦大泽之区,根本没有陆路、车道可通!是车骑兵与步兵行军的禁区!然而南北朝至今却有不少论者仍坚持认为曹操率领几十万大军是从江陵出发竟步行通过了云梦泽区,还居然把大本营屯置在此,实在令人难以想像!因为在这号称乌林的区域内,只有江侧黄蓬山等几个小山丘而已。正如《湖北通志》沔阳州(按:今洪湖市全在明清沔阳州内)下云:“自景陵至沔,迄于大江,绵亘四百里,皆漫然平衍,帷滨江数丘而已,谓之无山可也。”曹操东征孙刘位于前线的水陆大军至少有二三十万人马,怎么可能拥挤并屯住在云梦大泽滨江如此狹小的土丘之上呢?当然人们依据地形、地貌的科考也可能作出一些排除性判断,从而有助于赤壁战址的认定。就拿赤壁这种特殊地貌来说吧,顾名思义它应该是指赤色的山峦陡壁或者赤色陡峭的江岸。据《湖北省地理》教材介诏:“江汉平原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内陆拗陷的红层盆地,因为中部被第四系沉淀物所覆盖,只有在平原边缘才散见红层外露。”赤壁或赤岸的出现则与红层外露即本世纪普遍改称为的丹霞地貌密切相关。換言之丹霞地貌是出现是赤壁或赤岸的必要条件。南北朝时所提出的种种破曹战址,如不能满足这一必要条件者,首先就应将其从赤壁战址可能发生地剔除出去!既然靠考古发掘和依据地形地貌都很难对赤壁战址作直接界定,那么只有从历史文献上来追根溯源,才有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換言之赤壁战址以及与其密切关连的曹操进军、撤军的路线等等,基本上是一个必须依靠文献学来解决的历史地理问题。因此本书在史料证据的分析上与使用上纠正了南北朝及唐宋以降论者的误区而有所突破。本课题对充当证据的史料,分为了三类:甲,汉末魏晋时形成的可直接依据的核心史料——包括:⒈汉末至与陈寿同时代西晋时出现的主要史料;⒉东晋形成的次要史料;乙,南北朝出现的有争论、却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史料——包括:⒈与汉晋史料相吻合而不抵悖,则可与东晋形成的次要史料等同视之;⒉与汉晋史料相悖谬而必须淘汰或证伪的史料。例如:由盛弘之与郦道元倡和的赤壁战址蒲圻说竟以江南赤壁是黄盖诈降军队的出发地,上游一百六十里外的北岸乌林才是火攻破曹之地云云,显然与《后汉书·献帝纪》己揭示出赤壁与乌林紧邻的历史真相背道而驰,也直接与《三国志》中的《吴主传》《周瑜传》《黄盖传》《刘先主传》《诸葛亮传》《吕范传》《周泰传》中“战于赤壁”、“遇于赤壁”、“败于赤壁”、“拒破(或拒、或破)于赤壁”大唱反调,也同时与可靠的东汉史《后汉纪》卷30以及《华阳国志·刘先主传》等等关于周瑜战败曹操于赤壁的记载直接抵啎,这是首先必须予加以证伪和排除的。丙,唐宋至民国(至年)以地志与文人见解及民间传说的形式出现的史料。一般只能作为参考资料或考察的线索,而不能充当直接证据!凡可提供具体情形而与魏晋核心史料吻合无悖者,则可充当重要佐证,其中极少数通过大量实地考察而证实的情况(如清长江水师的《长江图说》),则可视为是对魏晋史料的某种证实。至于其在沿袭盛、郦二氏之说基础上演变流行的诸种赤壁战址说等(前二说见于《辞海》赤壁词条,后一说则由《大清一统志》首述),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异议,请联系编辑删除。联系
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jianglingzx.com/jlxxw/10650.html |
当前位置: 江陵县 >考证赤壁战址必须重视的方法论问题
时间:2021/8/12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直击江陵高考首日全县名考生开考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