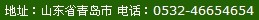|
一代梟雄項羽,在誅滅暴秦之後,表面上尊奉張楚懷王爲義帝,使之成爲名義上的天下共主。隨之,“項羽乃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並分封諸將相及業已自稱王號者十八人爲諸侯王(《史記》之《項羽本紀》、《高祖本紀》)。項羽所謂“西楚霸王”一稱,即由此而來。 這是關於項羽本事最早的原始記載,套用一個市面上很流行成語,可謂“自古以來”如此。可這“古”並不意味着一定是“真”。 一、“三楚”的地域觀念與 “西楚霸王”的窘境 世世代代讀《史記》的人,世世代代談論中國歷史的人,就這麼“西楚霸王”、“西楚霸王”地叫着,可大多數人根本沒想哪裏是東,哪裏是西,更沒想立都於彭城之地的這個諸侯王國到底該不該叫作“西楚”;即使有那麼很少一小部分人想了,分析了,也解釋了,可從來也沒有人解釋清楚過,甚至解釋了還不如不解釋,越解釋越讓人摸不着頭腦。 不管西楚,還是東楚,這“西”和“東”,都是以戰國的楚地來區分其相對方位。聽我這麼一說,大家一定急着想問:當時人所說的西楚究竟是在哪裏呢?其實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裏把這事兒講得是清清楚楚的: 越、楚則有三俗。 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已諾。 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夀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干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 通篇上下,談的都是西、東、南三楚之地的事兒,可前邊卻是以“越、楚則有三俗”這句話來提領其事。對這一點,唐人張守節在《史記正義》中解釋說:“越滅吴則有江淮以北,楚滅越兼有吳越之地,故言越、楚也。”這一解釋非常重要,也相當妥切,他告訴我們這三楚是兼有吳越之地的;也就是說,這西楚、東楚和南楚的地域範圍,從“楚夏之交”處的陳向南,直抵南嶺腳下,涵蓋南方大部分疆域(嶺南當時尚在趙佗南越國的治下)。至於確認這一點的具體意義是什麼,且容我在後面再來敘說。 現在,我們僅僅拿《史記·貨殖列傳》裏講的這個東楚之地的範圍,來對比一下項羽“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的屬地狀況,就會發現“西楚霸王”之稱所存在的問題。關於項羽封給自己的這梁、楚之地九郡,清代以來很多學者做過考證,但都未能盡得其實。周振鶴先生在研究西漢政區地理時,在前人的基礎上,對此做出了最爲真確的復原。下面這幅《項羽“西楚國”示意圖》,就是利用周振鶴先生《西漢政區地理》一書的插圖而改製的。 項羽“西楚國”示意圖 通過這幅示意圖可以看出,在泗水、碭郡、東郡、薛郡、東海、鄣郡(案應正作“故鄣郡,別詳拙著《建元與改元》)、會稽、陳郡和南陽郡這九郡之中,衹有陳郡一郡屬於《史記·貨殖列傳》所說“西楚”的範圍之內,最靠西側的南陽郡乃爲“夏人之居”,根本不屬於司馬遷所說楚地,北部的碭郡、東郡則應屬於梁地,也就是魏國故地及其鄰接區域,而“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這一表述,顯然也包括彭城和彭城所處的泗水郡在內(另外還應兼有文中沒有提及的薛郡)。唐人張守節在《史記正義》中就用李唐的政區名稱解釋說:“彭城,徐州治縣也。東海,郡,今海州也。吳,蘇州也。廣陵,楊州也。言從徐州彭城歷楊州至蘇州。”即以城邑論,彭城乃是所謂“東楚”的西端起點。過去有些人,如宋人孔平仲撰《孔氏雜說》,即強自把彭城解作“西楚”(見該書卷三),而這樣的解釋是完全不符合司馬遷本意的。 總括而言,按照《史記·貨殖列傳》的記載,可以說項羽留給自己的這個封國的國土即大多屬於“東楚”,國都也在“東楚”,即如清人錢大昕所云,“據此文,彭城是東楚,非西楚矣”(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録》卷一一“三楚”條)。居處在這樣土地上,項羽又怎麼能給自己定下個“西楚霸王”的稱號呢?豈不怪哉,豈不怪哉! 閱讀《史記·貨殖列傳》,思考西楚、東楚和南楚的地域區分問題,我們首先應該清楚,司馬遷在這裏講的是西漢前期人的地域觀念,而這也是目前所知距項羽生活年代最近的一種地域觀念。審其具體地域,如前所述,自是楚國滅越之後纔能產生這樣的觀念,因而若是沒有其他反證,這樣的觀念可以看作是從秦楚之際即已流行於世的。事實上我們在《史記》、《漢書》的相關注釋裏和後人的論述中也沒有看到比這更早的關於西楚、東楚以及南楚的地域認識。換句話講,《史記·貨殖列傳》上述記載,乃是後世學者解讀“西楚霸王”問題最早、最可靠的史料依據。 正因爲如此,我們看到,東漢末年至三國時期人文穎,在注釋《漢書·高帝紀》“羽自立爲西楚霸王”一事時,先是引錄《史記·貨殖列傳》的說法,以明三楚之說的歷史淵源,由於這淵源有自的說法顯然同“西楚霸王”這一名號相牴觸,於是文穎不得不綴加一句話,來勉強爲之疏說:“項羽欲都彭城,故自稱西楚。”這裏的“故”字應是用作“特地”之義,即項羽因立都於彭城,而強自把這裏稱作了“西楚”,意思是說,雖然這不符合通行的習慣用法,可項羽就這麼用了,我也衹能這麼說明一下情況。過去清人汪士鐸就是這樣理解文穎的說法,以爲“据此則彭城至項王始謂之西楚”(汪士鐸《汪梅村先生集》卷二《三楚考》)。文穎是老實人,說話做事兒就是這麼老實。儘管這話左支右絀,根本講不通,可他就是這麼實話實說,老實得實在可愛。 比他行年稍晚一點兒的曹魏時人孟康,就不這麼老實了。面對項羽這一奇怪的“西楚霸王”稱號,孟康先是把這一情況認定爲確切的史實(當然文穎也是對此深信不疑),然後放膽解釋說: 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漢書·高帝紀》唐顏師古注引孟康說。又《《史記·項羽本紀》之裴駰《集解》引孟康說) 這“舊名”二字就不是個話,你要真的有什麼根據就大大方方地說出來。孟康自己沒說,比他早和比他晚的那些其他的注釋《史記》、《漢書》的人也沒有別人見過他說的這種“舊名”,這事兒的真實性不能不讓我充滿疑慮。再說南楚、東楚和西楚,本來都是區域的稱謂,可孟康講述的“舊名”,卻成了江陵、吳和彭城這三處城邑的名稱,違逆正常的觀念和邏輯,顯然也很不對頭。 在我看來,孟康這種說法,乃是強不知爲有知,硬是以立都彭城的所謂“西楚”爲基點,強自給它配置上“東楚”和“南楚”;也就是說,項羽封給自己的這塊地方本來確實不叫“西楚”,可他自己既然這麼亂叫了,那“東楚”和“南楚”也衹能順着這個“西楚”來定。 大家千萬不要以爲這是我辛某人忽生橫解,厚誣這位孟氏夫子以心注史,清初著名輿地沿革專家顧祖禹,在引述孟康此語時就是如此看待這一問題,乃謂彭城之地本屬東楚,“項羽改爲西楚,而以吳爲東楚”(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二九《南直·徐州》。附案今中華書局點校本誤將顧氏這一判斷讀爲孟康注語原文,因而也就抹殺了顧氏的認識)。 這裏既以吳邑爲東楚,也就如同《史記·貨殖列傳》講述的三楚觀念一樣,衹能是在楚人滅越以後纔能產生,因而也不可能比《史記·貨殖列傳》的三楚觀念更早、更舊,其“舊名”云者,不過虛張聲勢而已。退一步講,這個“舊名”也衹是比孟康本人降生人世的時間稍微老舊一些而已,其事衹能像文穎所講的那樣,是因項羽自號“西楚霸王”之後纔產生的說法,更清楚地講,孟康所說“舊名”,就是從項羽分封諸侯時纔定下的嶄新的地理區域名稱。而包括今天我們這些人在內,後世學人在解讀《史記》、《漢書》中“西楚霸王”這一記載時,是萬萬不宜以後事來闡釋前因的。這樣做,太不邏輯。 清人錢大昕雖然極力想給項羽的“西楚霸王”之號的合理性做出解釋,可對孟康這一說法,卻衹是淡淡地講道:“此又一說,與《史記·貨殖傳》不合。”(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録》卷一一“三楚”條)顯然覺得要想合理地闡釋這一問題,還是應該依據《史記·貨殖列傳》來立論。書讀得多了,學問做得深了,至少有那個眼界,能夠及時躲開那些過分荒誕的認識路徑。 漢魏之際人文穎解釋不通項羽爲什麼自號“西楚霸王”,是因爲這“西楚”二字嚴重悖逆當時通行的地域觀念。 如上所述,緊繼其後的孟康,當然同樣也沒能講清這一問題。但由於再也找不到任何合理的依據,也講不出其他自成一說並足以服人的道理,後來裴駰在南朝劉宋時撰著《史記集解》,衹好照樣轉錄了孟康這一說法(《史記·項羽本紀》之裴駰《集解》)。到唐代初年顏師古注釋《漢書》的時候,也衹好稀裏糊塗地表態說“孟說是也”(《漢書·高帝紀》唐顏師古注)。儘管這種表態站隊在學術上並沒有任何價值,儘管後來張守節在開元年間撰著《史記正義》的時候,還是一併轉錄有《史記·貨殖列傳》和孟康各自講述的兩種“三楚”說法,儘量給讀者提供一個平衡而又客觀的參考,可是孟康這種說法,還是因顏師古的肯定而獲得了廣泛的傳播。譬如宋人孫奕的《履齋示兒編》、王應麟的《小學紺珠》等都是如此(《履齋示兒編》卷一四《雜記》“地名異”條。《小學紺珠》卷二《地理類》“三楚”條)。 這種“無厘頭”的說法,寫詩作文時當個虛頭巴腦的辭藻用一用自然無妨,可嚴肅的學者是無法把這當真事兒看的,清代的考據學家讀書讀到這裏時更不能不想來試試身手。 問題這實在是個難題,即使是當時的歷史考據第一高手錢大昕,也說不清是怎麼一回事兒: 《史記·貨殖傳》:“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此南楚也。”據此文,彭城是東楚,非西楚矣。項羽都彭城而東有吳、廣陵、會稽郡,乃以“西楚霸王”自號者,羽兼有梁、楚地,梁在楚西,言“西楚”則梁地亦在其中也。又考三楚之分,大率以淮爲界:淮北爲西楚,淮南爲南楚,唯東楚跨淮南北。吳、廣陵在淮南,東海在淮北,彭城亦在淮北而介乎東、西之閒,故彭城以東可稱“東楚”,彭城以西亦可稱“西楚”也。(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録》卷一一“三楚”條) 這段考證的要點有二:一是項羽乃“王梁、楚地九郡”,故雖然彭城地處“東楚”,但因“梁在楚西,言‘西楚’則梁地亦在其中也”,所以項羽纔會自號“西楚霸王”;二是彭城之地介乎“東楚”與“西楚”之間,“故彭城以東可稱‘東楚’,彭城以西亦可稱‘西楚’也”,實際上是說項羽所王九郡中的彭城以西部分,本來就屬“西楚”。 這兩點解釋,乍看似乎有那麼幾分道理,實際上都很不合乎邏輯。一者即使“西楚”確如錢氏所云可以兼該梁地,但這樣一來,泗水(治彭城)、東海、吳、廣陵等“東楚”之地怎麼辦?就爲照顧梁國舊地竟棄置國都所在的彭城於不顧而取“西楚”爲號,這麼說,能合理麼?我怎麼看都覺得很不合理,這太不合理了。二者項羽屬郡中彭城以西的陳郡固然屬於“西楚”,《史記·貨殖列傳》也講明了這一點,但這在其屬地中衹佔很小一部分,特別是項羽的國都彭城不屬“西楚”而歸於“東楚”,因而項羽更沒有道理會取“西楚”作爲自己封國的名號,即所謂“名不副實”也。 就連錢大昕這樣的一代考據大家也講不出個子午卯酉,甚至在他的考辨中還頗有幾分前言不搭後語的窘迫,這說明了“西楚霸王”這一稱謂確實是很難講得通的。明人陳士元評述“西楚霸王”這一名號,曾以“號爲西楚,本東楚地”這兩句簡簡單單的話,概括了這一稱號給人們認識這一問題所造成的窘境(陳士元《江漢叢談》卷二“三楚”條)。 二、不是“西楚”是“四楚”? 話怎麼講也講不通,這往往意味着認識的路徑根本不對。在這種情況下,通常就不宜一條道走到黑。變換一個認識的角度,也許會在我們的眼前展現出一片全新的天地。那麼,我們要把認識的角度轉換到哪裏去呢?陳士元“號爲西楚,本東楚地”這兩句話,提示我“西楚”的“西”字有可能存在問題——不是字譌,就是字誤,這個“西”也許應該是另外一個字。 下面的問題是,假如按照胡適之博士指示的治學路徑,先大膽假設“西楚”的“西”字存在譌誤,那麼,它應該是什麼字的譌誤呢?古代典籍的文字產生譌誤,最常見的形式有兩種:一種是因讀音相近造成的“音譌”,另一種是因字形相近造成的“形譌”。對這個“西”字,我首先想到的是字形相近的“四”字,即姑且假設“西楚”是“四楚”的譌誤,也就是原本的“四”字被錯譌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西”字。 歷史經過那麼久了。我們在研究歷史問題時需要注意,在關注每一項具體史事的時候,都應該基於這一事項後面普遍的背景。這樣,浮現在我們眼前的,就不僅是一時一事。我們需要意識到大多數事物都會有某些共同的規律性特徵,先人著述的文字錯譌也是這樣,而這種規律性特徵會爲我們提供一個基本的客觀可能性,作爲我們分析具體事項的參考。 因此,在“小心求證”上述假設之前,讓我們先來看一看“西”和“四”這兩個字,在古代,在當時,是不是存在相互致譌的可能。不管是“西楚”的“西”,還是“四楚”的“四”,都是作爲前置的構詞要素同後面的主體名詞組成一個複合名詞,衹不過一個屬於方位詞,另一個屬於數詞而已。這種構詞形式的相似性,是“四楚”錯譌成“西楚”的邏輯前提,亦即“西”、“四”兩字相互致譌之後,從表面上看,原文在邏輯上通常仍很通順,這樣纔會使讀者不知不覺地接受錯譌的文本,承認錯譌的文本。 接下來讓我們來看一下古代典籍中“西”、“四”相譌的例證。如《禮記·喪服小記》“及郊而后免反哭”句鄭玄注“墓在四郊之外”,即有刊本將“四郊”譌作“西郊”(王太岳《四庫全書考證》卷一二)。此類事例甚多,無須贅敘。 這一方面,在校勘學史上更爲有名的事例,也在“四郊”與“西郊”之間,也是出自《禮記》鄭注,即《禮記·祭義》篇“天子四學”句下鄭玄注云“周西郊之虞庠也”,其“西郊”二字在流傳過程中被譌作“四郊”,而唐人《禮記正義》的原本尚非如此(清顧廣圻《撫本禮記鄭注考異》卷下。《顧千里集》卷七《與段茂堂大令論周代學制第二書》、《與段茂堂大令論周代學制第三書》)。 清嘉慶丙寅張敦仁 仿宋刻本鄭玄注 《禮記》附張氏《考異》 這一事例,最易體現在特定的情況下“西”、“四”互譌是古文獻中極易發生的情況。粗略看上去,這兩個字的形態,就如同一個人扎了領帶或是沒扎領帶一樣,基本樣貌差不了多少,人們也就很有可能會把“四楚”當作“西楚”來看。 三、“四楚”的真相及其由來 既然就其字義、字形而言“四”字機易譌變爲“西”,那麼下邊大家就容我用“四楚”來替換掉“西楚”,看看項羽會不會自號“四楚霸王”。我知道,很多人看到這個說法,未免會覺得是“非常異議可怪之論”——你不認“西楚霸王”就改個“東楚霸王”唄,怎麼弄出來個“四楚霸王”?司馬遷本來說衹有西楚、東楚、南楚這“三楚”,你怎麼又整出個“四楚”? 大家若是覺得不可思議,下面不妨先從“三晉”說起。“三晉”是什麼,是韓、魏、趙三個故晉國境內的諸侯國,那麼好好一個晉國怎麼變成了“三晉”了呢?分的唄,韓、魏、趙三家瓜分晉土,各自獨立建國,這是開啓所謂“戰國”時期的標誌性事件,我想稍微瞭解一點兒中國古代歷史常識的人都會知道這一點。其實不光“三晉”是從一個整體中活喇喇地硬分出來的,“三晉”西面的“三秦”和東面的“三齊”,也分別是從秦、齊兩國故土上分割出來的三個諸侯國,只是其剖分爲三的時間要晚一些,是在大秦帝國滅亡之後,纔被項羽拆分出來,即項羽三分關中,封秦降將章邯爲雍王、司馬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成雍、塞、翟三國;項羽又將齊國故地一分爲三,分別封授齊將田都爲齊王、原齊王田巿爲膠東王、原齊王建孫田安爲濟北王,成爲齊、膠東、濟北三國。 “三晉”、“三秦”、“三齊”既然那如此,那麼,要是將楚國故地一分爲四,豈不就成了“四楚”?請大家看下面這幀插圖——它是從南宋建安黃善夫書坊刊刻的三家注本《史記·秦楚之際月表》中掃描下來的: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 南宋建安黃善夫書坊刻 三家注本《史記》之 《秦楚之際月表》 在“義帝元年”這一縱列之下,有“分楚爲四”四個字,這是我在這裏所要關注的焦點。至於我聚焦關注的是什麼,不用說,大家也都明白,那就是同“三晉”、“三秦”、“三齊”頗爲相似的“四楚”之地已經凸顯在我們的面前。 不過在具體講述這一記載之前,需要先對《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相關的內容做些基礎的校勘工作。大家看到的這個三家注本《史記》的《秦楚之際月表》其文字雖然存在一定問題,但比起現在同行的中華書局點校本畢竟還是要好出很多。更清楚地講,是今中華書局點校本《史記》的《秦楚之際月表》,被點校者以不誤爲誤,妄自刪除了原文當中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內容,因而我們在認識這一問題時不得不採用三家注本等早期刻本作爲論證的依據。 首先是在義帝元年這一列前面“十二月”那一縱列之內的內容,有些應歸入後面“義帝元年”這一列之下。這主要是和“分楚爲四”性質相同的“分趙爲代國”、“分齊爲三國”這樣一些內容。 這一列的“十二月”,是秦國的紀年,即子嬰就任秦王後所值秦曆的十二月。依本表,子嬰係於本年九月任秦王,而這一年爲秦二世皇帝三年。按理說子嬰已自行廢除帝號,退而稱王,宣告大秦帝國不復存在,本應當即改元,以示改帝年爲王年,可當時秦社覆亡在即,子嬰就這麼稀裏糊塗地即位了,並沒有改行新元。依據三家注本等傳世刻本和今中華書局點校本,“分趙爲代國”、“分齊爲三國”等等諸如此類的內容,就都被繫於這一年十二月之下。 可是這些史事都是同下一列裏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並分封十八諸侯事同時發生的,或者更準確地說,所謂“分國”正是項羽自立爲王及其分封諸侯的第一個步驟,是前後腳緊連着的事兒,在《史記》的《項羽本紀》和高祖本紀》中對此也都有清楚的記載——這一類事項同“分楚爲四”之事一樣,都被《史記·高祖本紀》記作義帝元年的“正月”。 這樣看來,像“分楚爲四”這樣繫年於義帝元年正月的欄下,應該是《太史公書》本來的面目,而那些繫在這上一年十二月下的“分趙爲代國”、“分齊爲三國”等同樣性質的內容,則應該是《史記》流傳過程中所產生的譌誤,是在後世寫錄刊刻時被錯移了位置。昔張文虎在清同治年間爲金陵書局校勘三家注本《史記》,不僅沒有能夠看出“分楚爲四”一語繫於義帝元年正月之下的正確性,反而依據梁玉繩《史記志疑》的謬說(見該書卷一〇),以不誤爲誤,將此四字挪移到前一年十二月下(張文虎《校勘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卷二),今中華書局點校本則不僅照樣沿承其誤,而且連個校勘說明都沒有出,普通讀者也就完全失去了探求的線索。 鳳凰出版社影印宋刻 十四行單附《集解》本 《史記》之《秦楚之際月表》 另外,在單附《史記集解》的宋刊十四行本《史記》上,我們可以看到,在義帝元年正月“分關中爲漢”那一行裏,書作“分爲關關中爲漢”(其上一欄裏已列有“分關中爲四國”)。聯繫上述情況,這裏看似增衍“爲關”二字,即似應當書作“分關中爲漢”,以與下一行的“分關中爲雍”、“分關中爲塞”、“分關中爲翟”相統一。可是這看似增衍的“爲關”這兩個字,提示我們在這一位置上本來應當同前面提到的“分楚爲四”一樣,寫有“分關中爲四〔國〕”的語句(這就是被通行文本中錯移到上一欄裏的“分關中爲四國”),而這“爲關”二字衹是這一語句剩存下來的一點殘痕而已(文字的順序且前後舛亂),從而愈加證明了上述分析的合理性。 進一步深究,還可以看到,即使如三家注本等書作“分關中爲漢”、“分關中爲雍”、“分關中爲塞”以及“分關中爲翟”,仍然不夠妥切。清人張文虎校勘《史記》,以爲“前表已書‘分關中爲四’,則此亦當如楚、趙、齊、魏、燕、韓例書‘分爲漢’、‘分爲雍’、‘分爲塞’、‘分爲翟’可矣。‘關中’字疑衍”(張文虎《校勘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卷二)。現在我們看“爲關”這兩個“分關中爲四國”之句的舛亂殘留,更有理由推想這幾個“分關中”云云的“關中”,應是《史記》流傳過程中受到原本中上面漢國一行“分關中爲四國”之句的影響而衍生,現在理應按照張文虎的推斷刪去。 按照這樣的認識,可將三家注本《史記》中相關內容復原如下: 三家注本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 相關內容復原表 爲了便於現代的閱讀習慣,我把原表文字的排列方向由從右向左改成了自左及右,但表格的編排次序並沒有改變,依然是右先左後。此外,表中用圓括號()括注的內容,是我爲便於大家閱讀附加的說明性文字;用梯形括號〔〕括注的內容,是原文有缺而敝人以爲應當補入的文字;用直方括號[]括注的內容,係原文所有而我認爲應當刪除的內容;用黑括號括注的內容,是我認爲此一黑括號前一字有誤而應當用黑括號內的文字來做替換。 在義帝元年正月這一縱欄內,我添加了一條豎線,把這一縱欄一分爲二。這樣的做法未必符合《太史公書》的原貌,但眉目清晰,便於大家理解相關事項的邏輯關係,希望大家給予諒解。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我從前一縱列“十二月”下後移到義帝元年正月欄內的文字,不僅限於“分趙爲代國”、“分齊爲三國”這類性質的內容,還有“項羽怨榮,殺之”和“羽倍約”、“臧荼從入”這三條記述。原因,是這三條記述的也是項羽分封十八諸侯的前提條件,這也就是前邊所說的項羽自立爲王及其分封諸侯的第一個步驟,即在這一意義上它同“分趙爲代國”、“分齊爲三國”之類的內容性質完全相同,所以這幾條紀事應是同樣被錯置於前一月下,現在理應一併重歸舊位。 另外,對表中校改的內容,在此也需要稍加說明。 具體地講,黑括號內的“黜”字,《史記》原文書作“殺”。今中華書局新點校本逕行刪去“殺之”二字,說明云:“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一〇:‘榮故(固?)在齊,羽安得殺之?《史詮》謂“殺之”二字削。’按:《漢書》卷一上《高帝紀》田榮被殺在二年春正月,本書卷七《項羽本紀》亦在二年,此時尚未被殺。今據刪。”今案一般校勘古籍的原則,是恢復原書本來的面目,而不一定非替古人改正其原稿的錯誤不可;即使非要去改,也一定要先最大限度地排除其他可能,再做改動。對像《史記》這樣的經典尤其應當如此。 這裏的“殺之”二字誠然不符合史實。容有舛誤,但卻不一定是增衍所致。因爲憑空增衍出這兩個字的可能畢竟太小太小,很難找到出現這種情況的緣由。換個角度,就古籍文字錯譌的原理來看,這“殺之”二字倒很有可能是其他文字的譌變。昔清人梁玉繩即曾提到“或曰‘殺之’當作‘不封’,又有本作‘怒榮叛之’”(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一〇)。綜合考慮相關情況,我推測這個“殺”極有可能是“黜”字之譌。 蓋田榮乃齊王儋之弟,當乃兄被秦將章邯誅殺後,齊人立故齊王建弟田假爲王,田榮怒,驅趕田假入楚,另立齊王儋子田巿爲王(《史記·田儋列傳》),自任丞相,操弄權柄。《史記·秦楚之際月表》上文在秦二世三年端月(即正月)下“齊國”欄內記云“項羽、田榮分齊爲二國”,指的就是他們各自操控的田假、田巿這兩個齊王。在這一前提下,“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招致項羽怨恨,所以在項羽主持分封十八諸侯時纔沒有得到王位,而所謂“項羽怨榮,黜之”,即謂項羽因怨恨田榮而黜落了他參與分封的資格,亦即褫奪了他獲取那個本應屬於他的田巿那個位置的機會。 在我把“項羽怨榮,殺(黜)之”這句話後移一月之後,這條紀事同項羽“分齊爲三國”而封之的前後邏輯關係便愈加凸顯出來。大家看看,這是不是文從字順暢達無礙呢?我想至少這要比活喇喇地割去“殺之”兩字會好許多。試思梁玉繩所說“不封”二字,與今本《史記》的“殺之”出入太大,文字舛譌,不易至此;另一方面,田榮直至此時也未嘗叛楚,衹是坐觀楚秦成敗而已,故亦無“叛之”之事可言。因知梁玉繩所引異說,都不能成立。 接下來再看“分楚爲四”這句話。審視下文“分齊爲三國”、“分關中爲四國”和“分燕爲二國”這幾條的表述方式,依通例,“分楚爲四”句末似亦應補一“國”字,即言“分楚爲四國”。又存世單行本《史記索隱》記述楚國之外其他諸國在項羽分封十八諸侯時被分拆狀況是“趙爲二”、“齊爲三”、“關中爲四”、“燕爲二”、“魏爲二”、“韓爲二”,其中齊、關中和燕的記述形式與今三家注本《史記》相同,而趙今本《史記》作“分趙爲代國”,魏今本《史記》作“分魏爲殷國”,韓今本《史記》作“分韓爲河南國”。觀《史記索隱》對趙、魏、韓三國的注釋分別爲“代、趙”、“魏、殷”和“韓、河南”,可知其所對應的《史記》原文必定是《史記索隱》載述的“趙爲二”、“魏爲二”和“韓爲二”。當年張文虎在爲金陵書局校勘三家注本《史記》時,即以爲“此表趙、魏、韓三國亦當如楚、齊、關中、燕例,疑《索隱》本爲是”(張文虎《校勘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卷二)。如果像今通行的三家注本那樣,書作“分趙爲代國”、“分魏爲殷國”和“分韓爲河南國”,這樣的注釋就疊牀架屋,多此一舉了(三家注本《史記》就是因爲這一點而在相應語句下略去了司馬貞的《索隱》,今中華書局點校本依樣畫葫蘆,也是連個校勘說明都沒出)。道理同前邊講述的一樣,即今三家注本等“分趙爲代國”云云的寫法,應該是《史記》流傳過程中在把這些內容改移到前格時無意間造成的文字譌誤。 明末汲古閣刻單行本 《史記索隱》 現在我在表中所做的訂正,主要參據的就是此表行文的通例以及單行本《史記索隱》所反映的古本舊貌。不過《史記索隱》“分楚爲四”句作“楚分爲四”,依通例當屬誤倒,張文虎在校勘《史記》時已經指出這一點(張文虎《校勘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卷二)。又單行本《史記索隱》“楚分爲四”條前有“十八國”三字,爲三家注本等傳世版本《史記》所無,而這三個字也應出自司馬貞所見《史記》本文。這“十八國”是針對衡山以下十八個項羽所封諸侯國而言,統而攝之,寫在這裏。依一般行文習慣,“十八國”前尚應另有一字,述其來由、屬性,故余臆補一“封”字,以成完句。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此表燕國欄內“臧荼從入關”的“關”字,是依據梁玉繩《史記志疑》的意見增補,不過梁玉繩並沒有講述這樣看的理由(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一〇)。其實衹有按照敝人的意見將這一紀事後置到義帝元年正月項下,纔能更好地理解司馬遷記述此事的用意和補入“關”字的合理性。蓋《史記·項羽本紀》載錄項羽分封臧荼事時記云:“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臧荼爲燕王。”這與《秦楚之際月表》之“臧荼從入〔關〕”句正相呼應。梁玉繩雖然從文句本身推斷當補入“關”字,卻未能識破這句話的內在涵義,所以他不僅沒有看出此句當後移一列,反而還以爲“此應書於燕二十七月”,即將其前移兩格,放置到劉邦入關中的“十月”項下(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一〇),實在差之遠矣。 四、“四楚”之國與項羽的“楚國” 在祛除種種衍生的譌奪之後,更加顯示出《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分楚爲四國”這一記載的實質意義及其合理性,這也爲求證“四楚霸王”的存在奠定了至關重要的基礎。大家看看,前邊我舉例子談到的“三秦”和“三齊”不是同所謂“四楚”在同一時間、出於同樣的原因而分置出來的麼?我們是不是越來越看到了“四楚霸王”這一假設的合理性? 歷史研究就像西洋人那句諺語所講的那樣,魔鬼就隱藏在細節當中。真心想要做歷史研究,真心想要看歷史的真相,我們就要耐得住心性而怕不得麻煩。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中麻煩的事兒還遠不止這些。下面這幾幀書影,取自中華書局本《史記》,是其《秦楚之際月表》中義帝元年前三個月的部分內容: (一) (二) (三) 中華書局點校本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 相關內容 對比一下前邊我出示的三家注本和單附《集解》本《史記》之《秦楚之際月表》,還有我復原的三家注本《史記·秦楚之際月表》,請大家看上面第(一)幀書影最上邊兩行的內容,其間最大的差異,是中華書局本把古刻舊本前三行歸併成了兩行;就此表的總體形式而言,是幾乎所有古刻舊本均開列二十一橫行,而中華書局本卻成了二十橫行。那少了的一行哪裏去了?——活活被校勘古籍的人吞到肚子裏去了。 這是一項嚴重的疏失;不,更準確地講,不能說僅僅是疏失,而應該說這是一個巨大的錯誤。因爲疏失是無意的忽略,而這裏的問題是人們對《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的有意更改——衹不過刊改者沒有把錯的改成對的,反倒是把對的改成了錯的。 爲便於大家對比參看,我先把古刻舊本《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相關內容略加考訂,摘錄於下。 古刻舊本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 相關內容表 覈實而言,這個大錯可謂久已鑄成,並不是中華書局本的點校者所獨創。其直接的前因,是承自中華書局本的底本、亦即清同治年間的金陵書局刻本(參據張文虎《校勘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卷二);若再向前追溯,則至遲梁玉繩在乾隆年間即已倡言此意(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一〇)。比老梁稍早,有個叫張照的傢伙,在給乾隆爺校勘武英殿本《史記》的時候,更自我作古,代替太史公重編了個“新表”,附在《史記》本篇的後面,自以爲“庶可識太史公之本意”(見殿本《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篇末附史臣《考證》)。不過從張照,到張文虎,他們都沒有任何版本依據,衹是個人主觀看法而已。中華書局點校本雖非始肇其禍,但最近這次重新點校其書,既然遍覈天下古本,也總應該在校勘記中對金陵書局本之外那些古老版本的情況予以說明。 中華書局點校本這一沿錯襲繆、改是爲非的舉措,情況相當複雜。對此,我在《史記新本校勘》一書中已經做過很細緻的考辨分析,大家若有興趣詳細瞭解,可以自己去查看(見該書第三篇第四節)。在這裏,衹是爲便於大家理解所謂“西楚霸王”問題,迻錄其中與此直接相關的分析,再略加發揮和補充。 簡單地說,古刻舊本《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在義帝元年之後開列的這二十一橫行,其第二行,是承續“楚王”的法統。大家看我復原的三家注本《史記·秦楚之際月表》,我把本表最開頭顯示每一橫行歸屬的“秦、楚、項、趙、齊、漢、燕、魏、韓”標記,列在了諸行開頭的地方,所謂“楚王”的法統就是由此承襲而來。請大家注意,這表格在義帝元年之前,本來是列作九個橫行的。司馬遷之所以把“秦”列在第一行,是爲了顯示秦轄治天下的地位。 可到義帝元年正月“諸侯尊懷王爲義帝”之後,“天下”的情況已發生很大變化。首先是義帝在形式上業已取代秦朝皇帝,成爲天下共主;其次是項羽正式頂替了楚懷王原來對楚國兵馬僚屬的統治地位,號稱所謂“西楚霸王”。但緊隨其後,甚至可以說是與之同時,“西楚伯王項籍始(德勇案:“伯”即“霸”之異寫),爲天下主命,立十八王”(過去我在《史記新本校勘》那部書中,曾主張把“西楚伯王”這句話讀作“西楚主伯”,現在看來是錯誤的,這裏改從中華書局點校本的讀法),這意味着項羽同樣繼承了楚懷王在滅秦之前作爲各路反秦力量之“天下”盟主的地位,“義帝”祗成了一個象徵性的虛銜。 請大家注意,作爲主命天下的“西楚霸王”,項籍的“霸王”之都是設在彭城。但在另一方面,“霸王”總得先是個“王”,項羽本人在由“魯公”晉升爲“王”之後,也要有個自己的“王都”,這就是古刻舊本《月表》第三行載述的江都。過去清人劉文淇寫過一篇《項羽都江都考》,很具體地認定過項羽以江都爲王都這一史實(見劉氏《青溪舊屋集》卷四)。 大家還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這一行是直接從本表作九橫行時“項”那一行延續下來的,而它上面那一行、也就是第二行的所謂“西楚霸王”行則是直接從本表作九橫行時“楚”那一行延續過來。這意味着所謂“西楚霸王”繼承的是楚懷王作爲諸方反秦力量共尊盟主的地位,而立都江都的衹是項氏自己直接統治的王國。 相互對比可知,從張照,到梁玉繩,再到張文虎,再到今中華書局點校本秉筆操刀的人,由於没有能够理解這兩橫行的來由,因而也就未能理解其性質,竟然妄自將原表第二、三兩橫行合併爲一行,並妄將原表第二行“諸侯尊懷王爲義帝”這句話上移到第一行,同時還徑行刪除了項羽“都江都”一事。這是多麼大的改變啊?還不出一句說明的文字,告訴讀者相關情況,以致你若不去閱讀古刻舊本,就會誤以爲太史公就把書寫成這個樣子了,後果真的相當嚴重——其最爲嚴重的消極後果,就是很徹底地泯滅掉了所謂“西楚霸王”的真相! 這就是項羽在“分楚爲四國”之後,他是一人兼具兩重身份:一重是所謂“西楚霸王”,這是一個“霸王”之國,從《秦楚之際月表》載述的情況來看,其都城似乎是設在彭城;另一重是四分之後的楚地之一國,這是一個普通的諸侯王國,都城設在江都。當然一人之身無法分作兩處,這實際上是有一個先後的次序,更有內在性質的差異,而正是這個先後的次序,向我們展現了項羽本人的諸侯王國同所謂“西楚霸王”之國的分別,透露出所謂“西楚霸王”的真相。 區分出項羽本人的諸侯王國與所謂“西楚霸王”之國以後,一個意想不到的問題,就忽地擺在了我們的面前:如果僅僅從字面上看“項羽乃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這段話,那麼這個“梁、楚地九郡”之王,似乎應該是指所謂“西楚霸王”。可如前所述,把“梁、楚地九郡”之地稱作“西楚”,這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通的;再說這樣一來必然會帶來一個很大的難題,即項羽本人那個以江都爲王都的諸侯王國又在哪裏呢?這看起來似乎很繞,但至少我們可以而且應該嘗試着按照這樣的思路把二者區分開來分析相關問題。 還是回到剛纔提到的認識路徑,這篇《秦楚之際月表》,至義帝元年發生了一項重要改變,即在形式上由九橫行改爲二十一橫行;實質內容上,則由陳涉揭竿反秦之初的秦、楚、項、趙、齊、漢、燕、魏、韓這九大政治勢力,改變爲義帝、“西楚霸王”及項羽所封十八諸侯國等二十餘股政治勢力。在這一改變發生之際,表中項、趙、齊、漢、燕、魏、韓諸項所涵蓋的地域範圍,實際上大體相當於戰國後期的楚、趙、齊、秦、燕、魏、韓諸國所控制的疆土,可以形象地理解爲“戰國七雄”重又並立出世。項羽自居爲王以及封授其他那十八諸侯王,就是以此地域空間爲基礎。 理解這一點之後,我們再來看這所謂“戰國七雄”是怎樣演變成爲項羽十八諸侯的。歸納起來,有如下三種形式。第一種,是被徹底剖分。“秦”亦即所謂“關中”之一分爲四(分爲漢、雍、塞、翟四國)就屬這種形式。第二種,是分出新諸侯國,剩下的原有王國更名。屬此類者有“趙”之分出代國之後,剩下的趙國故土“更名爲常山”;“齊”之分出濟北國和膠東國之後,剩下的齊國故土“更名爲臨菑”;“魏”之分出殷國之後,剩下的魏國故土“更爲西魏”。第三種,是分出新諸侯國,剩下的原有王國保持舊名不變。屬此類者有“燕”之“分爲遼東”後,剩下的燕國故土仍名之曰燕國;“韓”之“分爲河南”後,剩下來的韓國故土仍名之曰韓國。 那麼,同“西楚霸王”相關的那個“楚”呢?《秦楚之際月表》記述“分楚爲四國”之後,我們見到的情況是“分爲衡山”、“分爲臨江”、“分爲九江”,亦即從“楚”國之身分出了三個新的諸侯國。那麼,剩下來那一塊楚國故土怎麼辦了呢?單純從現在我們看到的這份表格來看,這實在很不清楚。依從第一種形式,可以理解爲被另分出一個名爲“西楚”的諸侯國;若依照第二種形式,則可以理解爲把剩下來的楚國故土更名爲“西楚”。但這兩種理解都講不通,即如前所述,其地理方位與時人的“西楚”觀念相牴牾,即按照當時的地理方位觀念,這裏更應該稱作“東楚”而不是“西楚”。 既然這兩種方式都不相符,那麼,就衹能是採用剩下來的第三種方式了——即“分楚爲四國”中那最後一國,沿承楚國舊名未變,徒稱之爲“楚”!驟然聽到這一推斷,很多人也許會感到驚訝。不僅《秦楚之際月表》,《史記》的《項羽本紀》和《高祖本紀》在載述項羽分封天下時都沒有提到這一點。人們感到驚訝是不足爲怪的,當然更多的人可能從來就沒有像我這樣思考過這一問題。 五、四楚霸王與滅秦之初 的政治地理格局 大家千萬不要以爲古往今來世世代代讀《太史公書》的人多了去了,該想,早就有人想了;若是沒人想,似乎根本就不應該像我這樣胡思亂想。實際的情況是,在認識古代歷史的過程中,很多人,很多學者,更喜歡把世人通行的看法當作確切無疑的史實,然後再恣意馳騁自己超乎常人的評判。 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把荒唐的認識當作真實的歷史來看,當作真實的歷史來講,這樣的事兒多了去了。像“始皇帝”本來是一個謚號性質的名號,故衹能用於趙正那個畜生的身後,那個畜生還活在陽世禍害天下蒼生的時候當然更不會這麼叫自己,這事兒夠有名、夠重大了吧?可中國的大學歷史教科書、中學歷史教科書,多少年來就一直講趙正那個畜生是“自稱始皇帝”(別詳拙文《談談“始皇帝”的謚號性質》,收入拙著《正史與小說》)。還有像楚漢相爭的決戰之役“陳下之戰”,千百年來,一直被誤稱作“垓下之戰”,現在中國的大學歷史教科書和中學歷史教科書也都這麼順着胡講(別詳拙文《論所謂“垓下之戰”應正名爲“陳下之戰”》,收入拙著《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世人也是篤信不疑。 其實若是閉上眼睛仔細想一想,就會發現,對待我們眼前正在生活着的這個世界,大致也是如此。這是人性的缺陷。瞭解到人性這一缺陷,我們就大可不必懷疑任何一項符合正常邏輯的思考,對自己,對他人,對世界,都是這樣。做歷史研究,就像胡適之博士講的那樣,認真讀書,虔心思索,先大膽假設,再小心求證就是了。 其實,關於項羽自封之國爲“楚”,這在《史記》當中的記載,是連篇累牘、目不暇接的。自從諸侯兵罷戲下,各自就國之後,《史記》述及項羽之國,都是以“楚”相稱,所謂楚漢相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以東者爲楚”(《史記·項羽本紀》),就是其最有代表性的表述。另外大家再看看劉邦在陳下(即所謂“垓下”)擊滅項羽而登基做皇帝後發佈的天下第一號詔令,便是封授韓信爲“楚王”,乃謂“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爲楚王”(《史記·高祖本紀》)。周振鶴先生復原韓信這個“楚國”所涵蓋的地域,謂“以秦郡言數自西至東當有陳郡、薛郡、泗水、東海、會稽等郡”(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大家對比一下前邊我出示的那幅《項羽“西楚國”示意圖》看看,這不基本上就是項羽故國的範圍麼?請大家注意的是,這個諸侯國的國名就是“楚”!它不是直接承自項羽的舊名又是承自哪裏? 按照這樣的認識,我在前邊出示的那份《古刻舊本〈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相關內容表》上,臆補出“楚”和“王項籍始。故魯公”這些內容,以與這一行後面的“都江都”三字相對應。竊以爲這是依照《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理當記有的內容,衹是在後世的流傳過程中脫佚掉了而已(另外這份表格中“韓國”一行稱韓成爲“故韓將”,“將”字應正作“王”。《史記·項羽本紀》記“韓王成因古都,都陽翟”可證)。 在認識到項羽自有的這個楚國之後,所謂“西楚霸王”的真相也就不難揭開了。 這就是項羽“分楚爲四國”的這四個諸侯國,除了項羽本人的楚國之外,其餘衡山、臨江、九江三國的國君,即衡山王吳芮、臨江王共敖和九江王英布這三個人,原來都是楚國的部屬。如《秦楚之際月表》所示,臨江王共敖爲“故楚柱國”,九江王英布爲“故楚將”,衡山王吳芮乃因率英布及越人起事反秦,並且把女兒嫁給英布,因而也是附從於楚(《史記·黥布列傳》。《漢書·吳芮傳》)。故簡單地說,這四塊地方,國是“楚”的地,王是“楚”的人,分之爲四國,合之當然可以稱作“四楚”,這同前面提到的“三秦”和“三齊”是同樣的道理。 “四楚”既然是一個理所當然的存在,那麼,所謂“四楚霸王”也就自然而然地顯現出來。在分封十八諸侯之前,項羽乘鉅鹿決戰獲勝的餘威,已經成爲楚國事實上的君主,分封天下時他從楚國故地中割出三塊區域,劃定衡山、臨江、九江三個諸侯國,分別封授給吳芮、共敖和英布這三個舊部屬。——正是爲繼續保持對這三塊土地和這三個舊日部屬的有效控制,項羽纔創製了“四楚霸王”這一特別的稱號,即謂他這一楚王仍有權力以“四楚霸王”是名號繼續管控衡山、臨江、九江這三個楚國舊境內的諸侯國,吳芮、共敖和英布三人舊日是楚臣,現在則依然是他這個“四楚霸王”的臣屬。 我們看就在項羽封授的各路諸侯就國之初,故齊相田榮就起兵奪權,自立爲齊王,項羽不得不統軍征齊,爲此,“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待後來“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兵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史記·黥布列傳》)。項羽這個楚王是王,黥布的九江王也是個一模一樣的王,項羽憑什麼就這麼大模大樣地“徵兵九江”?黥布爲什麼雖然自己“稱病不往”,卻仍不得不“遣將將數千人行”?到後來劉邦兵入彭城之後,項羽再一次徵兵九江,黥布則因“又稱兵不佐楚”而招致項羽怨恨,衹是礙於當時形勢纔隱忍未便加以討伐,這又都是爲了什麼呢? 道理很簡單,項羽這個“四楚霸王”對“四楚”之地都具有絕對控制的權力,除了直屬於他本人的楚國之外,衡山、臨江、九江這三個諸侯國也都要聽命於他。“四楚霸王”的“霸”字,首先就體現在這一點上。當項羽在彭城打敗劉邦之後,鑑於英布在楚漢相爭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劉邦遣隨何游說英布,勸誘其背楚從漢。當隨何問詢“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的時候,英布回答說:“寡人北鄉而臣事之。”(《史記·黥布列傳》)“北鄉而臣事之”這句話,明確無誤地表明了項羽這個“四楚霸王”與他這個九江王之間的君臣關係。 “四楚”之國的另外兩國、亦即衡山國和臨江國,也同黥布的九江國一樣受制於項羽這個“四楚霸王”。在楚漢相爭的過程中,由於實力和地理位置等關係,衡山王吳芮並沒有具體參與其間,而且在陳下決戰(亦即所謂“垓下之戰”)之後,隨即歸附於劉邦;而臨江一方雖然沒有參戰,卻一直忠實於項羽,在項羽敗亡於陳下並最終自刎烏江之後,始被劉賈、盧綰等擊滅亡國,而且即使是在這種孤立無援情況下,尚堅持數月之久(《史記》之《高祖本紀》、《荊燕世家》、《韓信盧綰列傳》、《傅靳蒯成列傳》)。 其實衹要老老實實地閱讀《史記》,自然而然地,都必定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手頭有一部《中國歷史地圖集》,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東北師範大學所編繪,用於中國歷史的函授教育。這本圖集中有一幅《楚漢戰爭圖》,標出了項羽所封十八諸侯國和他留給自己的那個“獨立王國”,而在這裏標記的項羽之國就是光禿禿的一個“楚”字,而不是像前後時期其他那些同類地圖那樣將其繪作什麼“西楚”(附案此圖標繪略有疏失,即圖例未注明諸侯國的王都乃用實心黑圓點表示。又原圖沒有以此符號注記代、薊、無終這三個代、燕、遼東之國的王都,而是標作表示“一般地名”的空心圓圈。此外,該圖用“國都”來標記“咸陽”,這也顯然很不妥當)!當然,你要是不深想,也不會理解到寄寓其間的其他那些歷史內涵,體會不到在這當中還有更大的名堂。 年東北師範大學 函授教育處出版 《中國歷史地圖集》 第一分冊 其實能夠體現衡山、臨江、九江三國隸屬於項羽這個“四楚霸王”的一個突出事例,是項羽在誅殺義帝時,是同時指令九江王黥布、衡山王吳芮和臨江王共敖將其擊殺於南去長沙郴縣的途中(《史記》之《項羽本紀》、《高祖本紀》、《黥布列傳》)。衹有對那些隸屬於自己的心腹,纔有權力、也纔有可能發佈這樣的指令。不說不知道,一說就很明瞭。 這樣看來,今本《史記》中所謂“西楚霸王”,理應是“四楚霸王”的譌誤,衹是這處文字譌誤產生的時間相當早,因爲我們看到東漢前期撰成的《漢書》就已經同樣誤書爲“西楚霸王”(《漢書·高帝紀》)。同這很相似的情況,有《史記·天官書》中五區星官的“官”字也都很早就因字形相近而被譌作“宮”,《漢書·天文志》襲用的就是這樣的文本,現在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依然如此。幸好唐人司馬貞著《史記索隱》時見到的本子還保持着《史記》本來的面目,使我們得以指實這一譌誤(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三)。由於世代相承,習非爲是,在此基礎上又衍生出很多似是而非的繆誤。現在我把“西楚霸王”這一譌誤揭示出來,或許會有一些人感到很不舒服(因爲這些人很不願意相信自己一直稀裏糊塗“將錯就錯”地在做研究),當然也更不願意接受,但正確的史實就擺在我們的面前,用這一史實來解釋相關的史事,可以說通體暢通,了無窒礙。硬要不信,着實也不大容易。 在復原所謂“西楚霸王”的真實面貌及其歷史內涵之後,我們纔能更好地理解項羽初封諸侯之時的中國政治結構,也纔能更好地認識當時的政治地理版圖。 項羽在分封十八諸侯之前,先“尊懷王爲義帝”(《史記·項羽本紀》)。本來這個“懷王”衹是反秦之楚國的國王,雖然這個楚國始建於首義的陳涉,並且在各路反秦力量中實力最強,影響最大,但具體的權力畢竟局限於楚,與反秦的其他各諸侯國,並沒有垂直的統屬關係。現在這個被項羽“尊奉”的義帝,在名義上,乃是統管全國的帝君。 不過給了這個名義,並不等於你就一定會有相應的能力去行使這個名義所賦予的權力。實際上這時義帝已經完全被項羽所控制,什麼權力也沒有,史稱項羽“實不用其命”(《史記·高祖本紀》)。劉邦攻入關中,拔取滅秦的頭功,本是緣於楚懷王有意爲之。這就是在項羽奉命北上救趙的同時,懷王刻意選派劉邦西略關中,並鄭重相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史記·高祖本紀》。案關於這一約定的原委及其歷史地理意義,拙文《論劉邦進出漢中的地理意義及其行軍路線》一文有具體的論證,感興趣的朋友可自行參看(該文收入拙著《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但項羽入關之後,並不想讓關中這塊寶地落到劉邦的手裏。當項羽向懷王請示處置辦法時,懷王卻堅持先前的約定,答之曰:“如約。”(《史記·項羽本紀》)。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項羽纔不得不走上前臺,直接“爲天下主命,立十八王”。義帝從表面上看,好像是較原先的“楚王”驟昇一格,轄有天下疆土,可項羽卻說本無滅秦定天下之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史記·項羽本紀》)。剛給個名義,還沒放手裏捂一下,就都讓項羽給分光了,而且乾乾淨淨地,一丁點也沒剩。更讓這位義帝窩火的是,自己原來的地盤楚國,這下子竟被項羽把表面上的名義也剝奪走了——項羽在名義上正式承續了楚國的法統,成了楚王,更在此基礎上進而成了“四楚霸王”,懷王衹落得個空頭的“義帝”。 不過即使是個空頭的“義帝”,也要有帝都。彭城這個地方,是當初項梁兵敗戰死之際,楚懷王從盱眙移居的都城(《史記·項羽本紀》);也就是說,從那時起,楚國的都城就一直設在彭城,楚懷王也一直住在那裏,到項羽將其“尊”作義帝時依然如此。劉邦起事反楚之後,在漢四年曾數落項羽的十大罪狀,其中第八條是“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史記·高祖本紀》),這說明在項羽“自都”於此之前,彭城乃是義帝之都,也就是全國的都城。 項羽把義帝逐出彭城,事在漢元年四月項羽從關中東歸之後。史稱“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史記·項羽本紀》)。從而可知,從這時起,彭城纔成爲項羽的都城,此前則爲義帝的帝都。這樣聯繫前面講述的情況,我們便能夠明白,項羽自己給自己的楚國擬定的都城江都,實際上他並沒有入住,而漢元年四月的彭城,纔是項羽楚國真正的國都,當然這也是楚國唯一的都城。至於所謂“四楚霸王”,由於這一霸王乃是項羽以楚國國王的身份兼有這一“霸王”的地位,自然也就沒有必要再爲其另設國都。 需要說明的是,這份《古刻舊本〈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相關內容表》所標示的義帝元年之二月、三月這兩縱列的內容,都同這兩個月份毫無關係。這些內容絕大多數都應該是在義帝元年正月這一個月內與項羽分封諸王同時發生的事情,衹是分作三個縱列分別標記而已。稍微有些特殊的,衹是表中第二行注記的“都彭城”,指的應該是漢高祖元年四月之後項羽楚國的都城,從彼時起,它也是“四楚霸王”的都城。 通過這樣的分析,我們可以把項羽初封諸侯時中國政治結構的基本形態,勾勒如下: 義帝元年政治結構 示意圖 通過這幅示意圖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全國的最高統治者,在名義上是義帝。但這個義帝的“帝”,同秦始皇創製的那個“皇帝”是完全不同的。即使是在名義上,它也不是一個集權統治者,衹是一個像上古聖明君主堯帝、舜帝那樣的帝位。當時實際控制天下的最高權威,是四楚霸王項羽,在名義上,他的位置是居於義帝之下的。四楚霸王項羽直接統轄有楚國這個諸侯國,但同時還對楚地分置的衡山、臨江和九江這三個諸侯國具有控制權,不過這種控制權是明顯弱於他對楚國的統治權的。對剩下的那十五個諸侯國,四楚霸王項羽則衹有一種“霸權”,即以“霸主”的地位威嚇震懾諸國,令其服屬於自己,而其實際效用如何,則衹能看當時的具體情況。 若是把上述認識,轉化到地域空間上去,我們就可以看到下述情況: 四楚霸王控制區域 示意圖 這幅圖同前面那幅《項羽“西楚國”示意圖》一樣,利用的也是周振鶴先生《西漢政區地理》一書的插圖,衹是按照上面講述的看法,適當修改了圖中部分內容。其中把韓國的土地也圈在“四楚”的範圍之內,是因爲“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史記·項羽本紀》)。從而可知,在分封十八諸侯之初,韓國的封地實際上也應入屬項羽的楚國管轄。 從這幅示意圖中大家可以看出,作爲“四楚霸王”,項羽能夠控制的地域範圍是相當廣闊的,相對於漢王劉邦,本佔據強大的優勢。項羽睥睨天下的“霸氣”,在很大程度上就應該出自這種地域控制的優勢——既不是所謂“西楚”,也不是什麼“東楚”,更不是那個“南楚”,而是包括全部楚地以及梁地還有所謂韓地的“四楚”。 這是“四楚霸王”一稱所體現的政治地理意義,這也就是當時政治地理格局的基本形態。楚漢相爭,就是在這一基礎上展開的,衹有認清這一基礎,纔能清楚理解楚漢之爭的全貌。 年3月8日記 年3月22日改定 此文今刊《澎湃新聞·翻書黨》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jianglingzx.com/jlxxx/9645.html |
当前位置: 江陵县 >世間本無ldquo西楚霸王rdqu
时间:2021/6/2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改名前的地名曾经多ldquo风雅r
- 下一篇文章: 一文看懂武昌城的前世与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