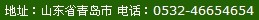|
怎样判断得了白殿风 http://news.39.net/bjzkhbzy/180606/6308431.html 一 陕西岐山县周原遗址出土了一批商末周人的甲骨,其中一片刻有“楚子来告”,这个楚子是不是就是春秋时楚国的先代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能加以说明。历史记载从春秋时期开始,楚国才不断地向四方八面扩展。《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方百里为同。楚武王和楚文王时(公元前年一前年,在位年,下同)楚国直属的境土,不过一百平方里;但到楚成王时(公元前年一前年),据《史记·楚世家》说,这时,“楚地千里”,发展了十倍。到楚庄王时(公元前年一前年),《韩非子·有度》说:“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进入战国以后,楚国一直不断发展,成为战国中后期的两大强国之一。后期战国策士假托张仪说,“秦地半天下”,“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侔交争,其势不两立”。当时的楚国,势力所及,与秦一样,也是“半天下”了。 战国七雄 在楚国不断强大和扩展的过程中,巴地部分不断为楚所侵蚀,蜀地南部边疆长期为楚所“包围”,直接地或间接地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发生了相当密切的交流和影响。早在公元前年,《左传》上已记载巴国君主要和邓国通好,还要取得楚国的同意和引进。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所以在巴蜀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许多楚文化的成分或因素。 《史记?秦本纪》说:“孝公元年(前年),河山以东强国六,……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从地形上看,自汉中向南,直到巴和黔中,当然应包括部分蜀地在内;而汉中广大地区内,属于蜀国的地方也不少。这可以说明巴蜀与楚国关系密切。《华阳国志?蜀志》叙秦灭巴蜀后,“赧王三年分巴、蜀置汉中郡”。可见汉中本为巴蜀之地。在此以前,同书还说:“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在秦惠王以前,蜀已占有汉中了。 战国后期形势图 《史记?六国年表》已明言汉中南郑一带,早在公元前年,即属于蜀国所有。在此时以后,秦国向南发展,和蜀国曾发生争夺南郑的战争。到公元前年时,秦伐蜀,取南郑。汉中成了秦、蜀拉锯争夺的焦点。但是,由于蜀国和楚关系密切,因而汉中又成了秦、楚争夺的焦点。楚国的鄢、郢,和汉中的地位一样,都是楚国必守之地。《战国策?楚策》上记张仪说:“为仪谓楚王逐昭睢、陈轸,请复鄢、郢、汉中。”国策此说乃说士虚构之言原不足信。《六国年表》载张仪死于公元前年,而楚失鄢郢乃在公元前—前年,去张仪死已三十余年,秦取汉中以任鄙为汉中守乃在公元前年。楚怀王死于秦之后,其时张仪死已十五年,张仪此说固不足信,但楚怀王时汉中属楚则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史记?屈原传》记屈原请杀张仪事也不可信)。 楚国的富强,是和他直接占有地域的广大,以及附庸国的众多分不开的。特别是它在春秋战国时代,楚国西境已达蜀郡西部金沙江流域。《韩非子?内储说上》记有:“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明言丽水(即金沙江)流域一带,西面可达滇池地区,属于荆楚所有。因此,得在此设官置吏管理黄金的开采。至于现在考古发掘出土的滇池周围或滇西的战国至西汉的文化中,所见到楚文化的因素,反不及蜀楚文化关系密切,其原因则因年代较后,又羼杂了自青海西康南下牦牛地区少数民族的影响。有人说滇西古文化与楚无关,这是错误的。 《史记?李斯列传》:“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郡,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巴、蜀、汉中、鄢、郢和九夷之地,均系自楚国夺取。不仅如此,黔中和巫郡,均系楚国故地,亦被秦夺取。《资治通鉴》:“周显王七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正义》:“楚自梁州汉中郡,南有巴、渝,过江,南有黔中、巫郡。”《战国策?楚策》亦言,由川东沿江上溯,南包夜郎,川、滇、黔广大地区均已属楚。《史记?秦本纪》:“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伐楚黔中,拔之。”黔中在蜀东南,故秦师因蜀而发兵。蜀人伐楚取兹方,亦应由此路而往。可能,黔中和巫郡一带,早时曾为蜀人的势力范围,后被楚所夺取,故楚人作扞关以御蜀。胡三省说:“秦兵时因蜀,出巴郡枳县,以攻楚之黔中。”正因黔中一带本为蜀地,楚地北接,秦灭巴蜀,秦兵得因蜀以攻黔中。《吕氏春秋》中曾记“吴阖闾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东征至于庳庐,西伐至于巴蜀”。当时吴王的目标是楚国,为什么要攻伐巴蜀呢?阖闾灭楚,当然被楚所侵略巴蜀旧境,亦因属楚而遭致攻伐。 《荀子?议兵》记楚国“汝、颍以为险,江汉以为池”。《淮南子?兵略训》:“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郯淮;颍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山髙寻云,谿肆无景。”这些具有实录价值的史籍,明白地指出楚和巴、蜀关系密切,巴、蜀为楚所“包”。巴、蜀的东鄙,北面和南面的土地,逐渐地为楚所并。而蜀之西南又为岷山庄王和夜郎庄王所据。看来,楚国包有巴蜀,并非夸饰之词。 “楚国包有巴蜀” 秦因与楚争天下,必需夺取巴、蜀和汉中,进而夺取黔中、巫郡,占据楚的大后方,居髙屋建瓴之势,对楚国形成严重的后翼包抄。在此一战略决策之下,果然击败了,当时与秦国同样“半天下”的楚国,完成了统一的大业。 楚国的政治势力,不仅达到了巴、蜀地区,还越过巴蜀,达到了今广西、云南和贵州等境域。《左传》襄公十三年记楚共王时(公元前—前年)“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公元前年(楚悼王二十年)以吴起为令尹,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吴起“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郤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盐铁论?通有》记“荆阳: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左陵阳之金,右蜀汉之材,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广而饶财”。这一切,充分看出楚国之所以成为战国中晚期的大国,是由于它幅员广阔,具有相应的强大的物质基础,必然形成的后果。广西平乐县银山岭发掘的一批战国中晚期的墓群,提供了确凿的实物,印证了史籍记载的真实性。如墓地集中,各墓排列有序,其形制都是长方形土坑墓,墓底大多设置腰坑,有的有棺有椁。随葬品除实用陶器,还有成套的铜、铁制兵器和生产工具。从墓葬形制到一些出土器物等,均与湖北、湖南等地楚墓极为相似,如长方形墓穴、腰坑、实茎剑、扁銎矛和戈、铁锄、铦刀等等。说明楚文化已经达到了这一地区。特别是在出土兵器上,有“孱陵”二字铭文,更足以说明问题。 古代从江汉流域,南至于海,西达滇西,地广人稀,《史记》称之为“陆梁之地”,时时出现瘴疠之气,古人对于大自然所作的斗争,颇为艰苦。就在早期的楚国领土内,《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僻)在荆山,筚路(素木车)、蓝缕(布缕无缘),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当时楚制度沿袭封建等级制,没有发展到中央集权制,贵族皆占有封地和私属,在政治上大大落后于秦晋诸国。到了楚悼王时,《吕氏春秋?贵卒》记:“吴起谓荆王曰:‘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余,臣不得而为也。’于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如此大量的无人或少人地区,不仅楚国直属的一些地区,如长沙、衡阳等地,是这种情况;许多边区国家及部落,如巴、蜀、南中各部,更是这样。这就给楚国贵族拓殖广大西南地区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些楚国贵族,或为戍守与长期驻屯,或为内部矛盾而远徙及此,或为有罪谪居,带领私属和一切动产,到新的地区定居下来。他们或与当地土著融合,“变服,从其俗以长之”,或较长期地保留了原有的文化。 《峝溪纤志》“苗族”里说:“宋家、蔡家,春秋宋、蔡二国之裔也,流而为蛮,性朴不诈,惟事耕凿,风俗略同,宋家稍雅,惟椎髻当前,衣冠尽废,宛然苗类。”这些宋、蔡二国贵族,被楚国灭其宗国后,移徙到了今贵州。李宗昉《黔记》:“宋家苗在贵阳、安顺二属,男耕女织,今多读书入泮者。”“蔡家在贵筑、修文、清镇、威宁、平远等州县;俗:翁媳不通言,居丧三日,不食稻肉,惟啜稗粥,夫死以妇殉葬,妇家夺去,乃免”。古代风习还保留了一些,正所谓“礼失而求诸野”。田雯《黔书》记:“宋家盖中国之裔,春秋时,宋为楚子所蚕食,俘其人民而放之南徼,遂流为夷,即宋宣慰之祖也。通汉语,识文字,勤于耕织。男子帽而长襟,妇人笄而短襟。”郭子章《黔记》与此大同。田雯还说“蔡家即宋人,亦为楚所俘”。看来,“移民实边”,是我国古代经常施行的政策,客观上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宋家等都是楚国开拓西南地区的先驱者中的一部分。据《汉书?扬雄传》,宋濂《宋学士文集?杨氏家传》和《平播全书》,播州杨氏应出于晋国叔向之后,逃奔于楚,辗转至黔。历唐及明,世为酋豪。 在今云南及滇黔、滇川界边著名的大姓爨氏,也是从楚国去的,他们祖先本身就是楚国的贵族。唐代著名的东爨和西爨中的许多乌蛮和白蛮,都因为长期受到楚国贵族爨氏的统治,而“从其酋长之姓”,因而以地域分为东西两爨;同时也说明爨氏在春秋战国时期到了南中以后,支系繁衍,族众盛多,已经一再的分族分部了。《刘宋爨使君碑》不仅是书法上的名帖,还具有很髙的史料价值。碑额上题“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碑文里说:“君讳龙颜,字仕德,建宁同乐(县)(人),(其)(先)(世)(则)(少)(昊)颛顼之玄胄,才子祝融之渺胤也。清源流而不滞,深根固而不倾。夏后之盛,敷陈五教,勳隆九土。纯化(洽)(于)(千)古,仁功播于万祀,故乃耀辉西岳,霸王郢楚。子文铭德于春秋,斑朗绍踪于季叶。阳九运否,蝉蜕河东,逍遥中原。班彪删定汉记,班固述修道(遗)训。爰暨汉末,采邑于爨,因氏族焉”。“迁避(运)庸蜀,流薄南人(入),树安九世,千柯繁茂,万叶云兴”。此碑在云南曲靖陆凉蔡家堡爨君墓前,碑高丈余,有穿有阴,额在穿上。碑中所记楚之远祖颛顼祝融等,是有文献与出土文物可征的。还说到楚令尹子文及汉代的班氏,皆属其同一宗族的分支。《风俗通》亦明言“斑(班)姓,楚令尹斗斑之后。”斑为子文之子,《左传》作般,犹公输般,一作班(斑)。楚国王族的这一支系爨氏后嗣,先到了蜀地,再分散到西南地区,世为大姓,历汉末直到隋唐,传十余代,皆为酋豪或羁縻州郡首领。诸葛武侯南征,收其俊杰建宁爨习,官至领军。碑文中说:“迺祖肃魏尚书仆射河南尹”,爨龙颜即其玄孙,与郑樵《通志》爨氏条相合。李雄时爨深为交州剌史,梁武帝时爨瓒作宁刺史。瓒子翫,降于史万岁,入朝被戮,其子弘达,唐武德中为昆州刺史。《南诏德化碑》有南宁州都督爨归王,昆州刺史爨日进,黎州刺史爨祺,求州爨守懿,螺山大鬼主爨彦昌,南宁州大鬼主爨崇道,后晋有爨判,曾借兵给段思平,以败杨干贞。爨氏源远流长,史迹信而有征。该碑碑阴列名中,约十人均属爨氏一系,分担各种职责,亦说明当时爨龙颜一支,已是族众不少了。 爨为统治部族,僰则为其部民,爨氏分族段氏,本系同一族属。爨、段同在广韵去声二十九换韵,并为同音异写。而在元、明之时,爨、僰有时写爨,有时写僰,可以代用,皆为一种。此即《元史?兵志》上的“寸白军”。李根原大理国张胜温梵画长卷:“滇中旧世家,先爨而后段;爨段本同音,东西各分半。”此说符合历史实际。追本溯源,建立大理国的段氏,其先亦应为楚人。《大理三十七部会盟碑》立于大理王段素顺明政三年(年),康熙十八年(年)出土,碑尚存于曲靖第一中学。碑文题名中有“三军都统长皇叔布变燮子王示(斜王旁加示字)”、“都监三军礼乐爽长驸马布变燮彦贞”、“侍内官久赞段子惠”等人。这些段氏宗族统辖之下的各部,其族属并非单一,原先乌、白蛮及其他部落和部族,均属大理臣民。因而表现为一种复合文化。《土官底簿》明白提到明时的许多段氏土官,均系僰人族属,足以印证上述论点。僰人与楚人关系极为密切,原为楚国的移民。这点后文再述。 至于古代楚人去西南地区的交通要道,(大约可循三条路线。一为汉中大巴山线路。既可赴巴,又可至蜀;其北端可能与《国策?秦策》上所说“栈道千里,通于蜀汉”的线路衔接。一为沿川江线路,经夔巫而达枳与渝,再经汉之僰道,以达南中。其中川江一段,并非水路,因三峡一带,极不适于航运。扬雄自述其先祖由楚至蜀,据《汉书?扬雄传》,即曾经由此路,然后才到蜀地。一为循清江和沅江,经黔中、且兰,鄨(约今遵义)为其中心枢轴地区,夜郎庄王(庄蹻)即经由此路,由楚而至夜郎。当然,不是说仅此三条线路,除此而外,肯定还有不少通道,但文献无征,年湮代远,已不易指实了。 南宋时期的大理国 二 楚在商、周时代,或称为荆,《诗经》有“蛮荆来威”的诗句;或称为楚;或合称荆楚,《诗经》有“奋伐荆楚”的诗句。它和蜀的关系,可以推溯到较早的古代。 关于荆人鄨令的史迹,不见于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而见于较常璩早约百年的来敏所撰的《本蜀论》,此书久已亡佚,《水经注》引用两条,其中之一,记述望帝故事,见《水经注》卷三十三:荆人鄨令死,其尸随水上,荆人求之不得。令至汶山下,复生,起见望帝。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为宇妻,遂王于蜀,号曰望帝。望帝立以为相。时巫山峡而蜀水不流,帝使令凿巫峡通水,蜀得陆处。望帝自以德不若,遂以国禅,号曰开明。除去传说中的不合理成分,当有所依据,并非杜撰;其母题或素材的时代,显然是相当早期的,国家出现以后,是不会行“禅让”之制的;只有在排除水患以后,成都平原才得以“陆处”,这一点和古代盆地的基本地理,完全符合;江源女子朱利与望帝,是两个互通婚姻的部落或胞族,当为一个族属,来自江源。 应劭《风俗通义》亦云:“使鄨令凿巫山”;许慎《说文》中亦提到“蜀王望帝”私其相之妻。可见这一故事在两汉时,是颇为流行的,虽然情节有些差异。 旧说《蜀王本纪》作者扬雄,误,实为谯周之作;谯周荟萃《蜀王本纪》或《蜀本纪》,对此故事,颇有增改,可能另据别本。但其基本点之一的荆人令,却是共同的。 《华阳国志?蜀志》称“开明,……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让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这些内容,仍与来敏和谯周所传相似。常志还说:“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这里明确指出蜀人音乐与荆相同,乃自荆人引来。而此荆乐之到蜀地,又是和开明——荆人鄨令分不开的。 综上所说,我们大体可以判言,蜀地古代的重要首领开明氏,本来就是荆楚之人;他来到蜀地,并不如传说那样,是一个死而复生的人,这显为历代附会,或当时故神其事,以表现其部落首领之不同凡流。而他之来到蜀地,从鄨邑渡赤水河以至江北而达蜀境。先到岷江与青衣江一带,《太平寰宇记》云:芦山县亦古严道县地,地志还说芦山县“治有开明王城故址”。《华阳国志?蜀志》亦言“蜀王开明以灵关为前门”,《太平寰宇记》云:灵关山在(芦山)县北二十里。这些遗迹的出现,当非偶然。开明氏及其部落带来荆楚之人的音乐,必然还传播其他一些荆楚文化。 商周人面鱼鸟箭纹金王冠带金沙遗址出土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楚、蜀的关系,更为密切。 春秋中期,楚国开始在云南楚雄设官置吏,管理丽水黄金的开采。《韩非子·内储说上》: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人多窃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辄辜磔于市;甚众,壅离其水也;而人窃金不止。为了垄断黄金,楚国统治者用严刑峻法禁止人民窃采。韩非当时就亲身见闻所及,成此实录,颇具信史价值。 解放后,湖南省博物馆在长沙、常德、衡阳等地,发掘约三千座楚墓,其中百余楚墓中,都有随葬的天平用的砝码,一些墓中还出土天平。这种天平仅有一公斤以下的砝码,就说明它只能作为衡量贵重金属——黄金之用。 《竹书纪年》是出于魏襄王坟墓里的竹简书,所记六国时事,都是当时第一手材料,较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更为翔实可信。“岷山庄王”即见于此书。蜀郡严(庄)道,原以岷山庄王居此而得名。岷山庄王是楚国贵族所建立的王国之君,是楚王在丽水地区的代理人。他和夜郎庄王一样,是楚庄王的后裔,以庄为氏。这两个庄王的详析史迹,见于《试论岷山庄王与滇王庄嶠的关系》。 年四川荥经县古城坪城关镇砖瓦厂,在距荥经县五至六华里处,发现并清理了三座战国至汉初时代的古墓,随葬器物中有铜鍪、铜勺及木胎漆器数件,其中漆耳杯上还有朱书“王邦”二字。据说此墓旁尚存有大墓数座。清理的三墓中另两座(一座残)时代稍晚,出土了“八铢半两”。墓葬形制与楚墓对比,颇有相似之处。可能属于岷山庄王(从春秋战国延续到秦汉之际)宗嗣子孙的茔地。 三 蜀地在古代,除了开明氏、岷山庄王和夜郎庄王与荆楚有密切关系外,楚国还有斗氏、扬氏、樊氏、昭氏等,亦在蜀地活动,其中一些部族,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蜀地的开发和促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余年间,楚国执政大臣斗(鬭)氏,史不绝书。武王通时,有斗伯比、斗祈;成王恽时,有斗谷菸莬、斗勃、斗宜申;庄王旅时,有斗班、斗椒;前后见于史籍者达二十人以上。《左传》宣公四年,楚若敖娶于?,生斗伯比。是斗氏出于楚之王族。子孙繁衍,长期为楚重臣。另外,一些宗支却移徙拓殖到了蜀地及其西鄙。《史记·西南夷传》称,杀且兰邛君,并杀笮侯。当时阻通滇道乃后来爨氏所统治的同乐。岷山和夜郎两个庄王,是楚王近亲,属地大,称王;笮侯(即笮人的统治者)乃斗氏之后,与王室疏远,故称为侯。他们的后嗣在历史上,散居于益州、南中、戎州、雋州和黎州的广大山箐谷坝之中,与僰人融合为一,成为僰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僰人的著姓大族。很有可能,僰人本是楚国居民中的重要成分,僰为棘人,即荆楚之人。他们生活在农村公社之中,周围不是构筑城墙,而是用荆楚或棘围以作防御之用。楚有棘围,见于《国语?吴语》,《左传》昭公十三年作棘闱。《吴语》中记楚灵王时内外溃叛的情况:“王亲独行屏营彷徨于山林之中……乃匍匐将入于棘围,棘围不纳。”这些用荆楚作为棘围的人,自然就是僰人了。 有些楚人,来到了蜀地,和土著僰人结合,或“变服,从其俗”,自然地融合于僰人之中了。现在,根据他们的姓氏,得以寻根究本,明了其渊源所自。《礼记?王制》记有“屏之远方,西方曰棘”的说法,它和先秦史上常见的徙民若干家和移民“实虚广之地”相符合。因而,我们对《礼记?王制》的记述,不能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可见蜀中古僰侯之国,和开明氏时的蜀一样,与楚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汉书·扬雄传》:“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侨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晋之扬,因氏焉。不知伯侨周何别也。扬在河、汾之间。周衰而扬氏或称侯,号曰扬侯。会晋六卿争权,韩、魏、赵兴而范、中行、智伯弊。当是时,逼扬侯,扬侯逃于楚巫山,因家焉。”扬氏在晋失败后挈其家族投奔于楚,因为他们是楚之邦属,故多处于边疆,这一层是明确的。这时,正是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按古代习俗,这种逃奔,必携其族系,挈其重器,连带掌握工艺技能的劳动力,全都移徙到了楚国巫山一带。然后,重新开发山林,建设家园。一些支庶子孙,又辗转经由巴地江州,到了岷山之阳的郫地定居。扬雄即属于到了蜀之郫地的一支。其祖先“有田一廛,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年湮代远,“沧海桑田”,食采的扬侯之后,已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农民。在三国蜀汉时,成都平原尚地广人稀,诸葛亮还从边区移民于此,战国、秦汉之际,较诸葛亮时,蜀中人口当更为稀少。扬氏由河东到楚国,再到蜀地,在这一过程中,当然需要“变服,从其俗”。随着巴蜀的逐渐融合于秦楚或中原,到了西汉时,扬氏自然和编户齐民没有二致了。 宋人赵明诚《金石录》记有今雅安地区芦山县《樊敏碑》文。此樊氏亦为晋国叔向之后,在晋国六卿争权,国内混乱残杀时,和扬氏一样,逃出晋国河东,以樊为氏。先在楚国定居,然后辗转到了蜀地。所以在建安十年《樊敏碑》上说:“君讳敏,字叔达;肇祖虙戏,遗苗后稷;为尧种树,舍漆从岐。天顾亶甫,乃萌昌发;周室衰微,霸(云)伯匡弼。晋为韩魏,鲁分为扬。充曜封邑,厥土河东。肆汉之际,或居于楚,或集于梁。君缵其绪,华南西疆,滨近圣禹,饮汶茹汸。”碑文上清清楚楚地说明了,蜀中樊氏为姬姓周人之后,曾在河东一带活动,后来到了楚国和蜀地。因此,他们也会带来不少楚文化影响。 扬雄和樊敏原属同族的两支。《汉书·地理志》河东郡有扬县,应劭云“扬侯国”。春秋时扬为叔向食邑。叔向兄弟四人铜鞮伯华、叔向、叔鱼、叔虎,因晋国内乱,伯华、叔向被囚,叔鱼逃奔于鲁,叔虎被杀。《樊敏碑》上说“鲁分为扬”,即指叔鱼之事。到《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前年)晋杀叔向之子扬食我,遂灭羊舌氏。扬氏在晋被灭,其族人子孙或即由晋逃奔于楚。《樊敏碑》说:“或集于楚”,应属此时之事。《扬雄传》上说:“逃于楚巫山,因家焉”。当时各国争霸,楚国当然收容晋国亡人,并优礼有加。或即以襄樊一带作为其中一些亡人的食邑。襄樊名称,亦当由此而来。叔向先代,出自周之阳、樊二邑,其在晋称扬肸、扬食,即因出于阳邑之故。《樊敏碑》记樊氏“或集于楚,或集于梁”,樊氏迁梁,就是在居楚之后。但当白起拔鄢郢,楚国东徙于陈之时,樊氏早就由汶川、什邡进入蜀郡的青衣道了。《竹书纪年》载梁惠成王十年(前年)“瑕阳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来归”,瑕为晋地,战国时属魏,结合《樊敏碑》研究《竹书纪年》的这一史料,不仅说明《竹书纪年》等史籍并非什么“断烂朝报”,还充分看出了古代巴蜀与楚国和中原的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政治影响。 楚国昭王在位二十七年,有复楚之大功,子孙繁衍,以谥为氏。楚国贵族屈、景两个大的姓氏之外,又增加了昭氏,成为楚国三大贵族之一。战国时昭衔、昭阳、昭鼠、昭睢、昭鱼、昭常、昭过、昭奚恤等等,皆楚国大臣,即属于昭氏,为楚昭王之后嗣。昭氏的支系,凭借楚国为七雄中的大国,发展拓殖到了蜀地。昭鼠在楚为“宛公”,实即宛尹;昭奚恤为楚相时,北方各国均以其代表楚国,皆对昭奚恤甚为畏惧,江乙更与魏国合作,多方排挤和陷害昭奚恤;昭常入则与王议论国事,出则典守楚之东地五百里,与齐抗衡。昭氏世为楚国大臣,驻守蜀地的可能性极大。《晋书?苻坚载记》述当时童谣:“河水清复清,苻诏死新城。”苻诏即苻坚。晋时苻诏的诏,和唐代南诏的诏,以及云南境内的一些土司以召或刀(刁)为姓者,均有可能与楚国贵族昭氏有关。 四 年,新都战国土坑木椁墓的发掘,从墓葬形制到腰坑出土的一八八件铜器,完全可以证实上述我们提出的古代楚蜀的密切关系。 墓葬平面、纵剖面、横剖面图 新都战国墓中出土五件铜鼎,其中一件盖内有“邵(昭)之飤(食)鼎”铭文。“邵(昭)”字及字体风格和安徽寿县蔡侯墓以及湖北的一些楚墓铜器上及其他器物上的铭文,十分相似。“鄂君启节”是楚文物中的一项重器,其中“邵”(昭)字和此鼎盖铭文,亦合。“邵”之为“昭”,文献上和出土实物上均有铁证,无庸置疑。《史记?甘茂列传》引范蜎对楚王说:“且王前尝用召滑于越,而内行章义之难,越国乱,故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计王之所以能如此者,越乱而楚治也。”《战国策?楚策》上也记有召滑史事,与上引《史记》大同,唯蜎作环,或作蝝、蠉。《韩非子?内储说》引干象对楚王语:“前时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者,越乱而楚治也。”《战国策?赵策》提及此邵(召)滑时,又作淖滑。《战国策?楚策》又作卓滑。贾谊《过秦论》上直作昭滑。可见,召、邵、淖、昭等,古代字音均可通假。湖北省江陵县马山区滕店公社望山大队境内望山二号楚墓,为一有大封土堆的土坑木椁墓。内椁与内棺之间,四周各盖一木板,南边一块盖板上刻有阴文印章,文为“邵吕竽”,同样的印章在同一块椁板上刻了六处。方壮猷同志释为“昭闾于”或“昭闾鱼”,极是。《史记》和《战国策》中不止一次地提到楚相昭鱼,应即此人。新都出土铜鼎盖内铭文上的“邵”字,不仅与江陵望山楚墓“邵”字相同,而且还和寿县楚墓“昭”字相同。其他周代的十余个器物上的“昭”字,均与新都铜鼎“邵”字类似。有人说此字为“启”,牵强附会,实不足取。 邵之飤鼎 邵之飤鼎铭文拓片 楚国贵族昭氏的器物,为什么到了蜀地?一种可能:昭氏支裔,到了蜀地,或为驻守,或为监管,有如西周初年的三监。一种可能,蜀人强取于楚或由楚赏赐而来。 我们认为,后者的可能性小,于史无征;前者的可能性大,史有遗迹。 从春秋战国的历史看来,蜀国和楚关系十分密切,已如上述。当时楚蜀的关系,因蜀僻在西鄙,而楚不断壮大,北上争霸,问鼎中原,东抗吴越,拓地至于海滨,只要蜀国和楚保持一定关系,就可相安无事。据《史记?六国年表》和《楚世家》,蜀曾伐楚兹方,“蜀伐楚戒兹方,于是楚为扞关以拒之”。其时在公元前年,正当吴起在楚国变法之后。蜀楚兹方之战,在国力悬殊下,很快地即以蜀之撤退告终。兹方,据《正义》,在荆州松滋扞关,据《太平寰宇记》,在今湖北长阳县,位于兹方西面,故可断言蜀人向西退回后,楚人才能在扞关进行防御设施。在这种情况下,蜀人要虏掠许多的楚器,有很大因难。至于因为蜀王为楚之西鄙君主,要用这样多的精美的铜器(重器)进行赏赐,也是不好理解的。特别是蜀王的墓葬,完全没有必要按照楚人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进行埋葬。蜀王总应该有他的自己的特色和风格。但是,墓葬形制,铜器形制,特别是铭文,反映出的却是楚文化。联系到楚国贵族昭氏极有可能屯驻蜀地,新都战国墓的一系列现象,就比较地易于解释了。 沈仲常同志曾经指出此墓具有相当浓厚的楚文化因素,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座较为典型的楚文化的墓葬,颇有根据。椁室内有头箱,左、右边箱和足箱,身份与诸侯相当。且在腰坑和墓中使用了白膏泥,均与楚墓类似。随葬铜器的组合,有鼎、敦(球形)、壶(加盘、匜、勺),还出土有似平顶合碗形的敦。与楚墓对照,似为战国中后期的墓葬。文献上的史证和出土的地下实物,如此紧密地直接结合在一起,是很可以说明问题的。 以出土文物说明古代楚蜀关系的墓葬,除了荥经、新都的战国墓外,还有涪陵小田溪土坑墓、成都羊子山一七二号墓和青川墓群等等。 涪陵小田溪出土了青铜乐器、兵器和生活用具。其中编钟十四件,用错金技法,铜壶用错银技法,均饰以精美纹饰,巧雕细镂,反映出当时工艺水平的高超。这批地下文物,无论就形制、花纹、图案等方面观察,有许多都和楚器相似。出土的一件铜戈上,刻有细如毫发的铭文“武二十六年蜀月武造,东工师宦,丞业,工篪”。字体类同于秦篆。似为秦昭王二十六年之戈。涪陵古为巴地,但战国以后,和蜀的交往加剧,关系密切,有渐趋同一的迹象。如新凡水观音遗址,彭县竹瓦街窖藏,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广汉中心遗址等蜀地早期遗存,与中原殷文化相同;与战国时期的蜀文化有不少差异。至于战国时期的蜀文化却和巴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足以窥其异同渗透之迹。 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出土铜壶 成都羊子山一七二号墓,葬式与楚墓相类,墓四周和墓底有厚约0.5米的膏泥。在丰富的随葬品中,有不少巴蜀时期常见的器物:也还有不少器物,和楚器十分一致。墓主人没有佩带蜀人常用的所谓柳叶形铜剑,而佩带的是楚式剑,亦可说明问题。 成都羊子山号墓铜矛錞身与楚器上相似的银错花纹 青川墓群,就已清理的来看,形制和器物上,均有相当成份的楚文化;特别是其中一部分漆器,和楚国漆器比较,颇为类似。很有可能,古代楚国的漆器,许多均由蜀地传播而来。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一、三号墓出土了近五百件完整的漆器,其中一部分漆器上烙印“成市草”、“成市饱”等戳记,证实了这些漆器产自当时蜀郡成都的市属手工作坊。青川墓中出土的一些漆器上有“成亭”字样,当系来自成都的官手工业。古代蜀地以产漆器著称,并远运至国外,如朝鲜等地。以此,我们说楚国的漆器大量来自蜀地。西汉著名的“蜀漆”,当非一朝一夕而起,可能在春秋战国时,已逐渐萌芽和发展。广汉蜀郡工官乃蜀地传统文化,应有其悠久历史。他如金银器、火井、盐井、流泉、栈道等,皆蜀地文明高度成就。蜀文化受楚文化影响,楚文化中亦有蜀文化影响。同样,在巴的地域内,有些墓葬曾出土楚国的兵器、生活用器、礼器和酒器,以及和楚地相同的器物组合;而在楚境内,也常有巴人的器物出土。 古代楚蜀之间,关系密切,相互交流和往来,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他们为开发我国西南山区和缔造我们历史悠久的文明祖国,并肩劳动,共同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近年来,在古代蜀地出土了许多包含楚文化因素的遗存;对于这个现象,书缺有间,其详析情实,还不能确知。本文试图钩稽文献记述,加以分析,以对此等现象的出现,进行解释,并清理其脉络渊源的史迹。我们相信,在今后的考古发掘中,还会不断地在古巴蜀地区出土楚文化遗存。 来源:《文物》年第6期,收入《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 转自:守靜齋主公号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jianglingzx.com/jlxtq/10642.html |
当前位置: 江陵县 >徐中舒丨古代楚蜀的关系
时间:2021/8/12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6月24日早安middot荆州丨最高
- 下一篇文章: 吴江到江陵物流专线五金配件长途搬家摩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